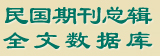当前位置:期刊浏览>東方雜誌>1930年 27卷> 第 22 期
詩人朗佛羅
作者: 文章来源:東方雜誌 发表于:年 卷 第 期 发表时间:民国19年22 ( 1930 ) 栏目:—
我和 父锌确靠愈邢娱形靈影君在P巿保衞界的馬路旁散步,徐徐地前進;心裏感到父锌确靠愈邢娱形一種輕鬆的愉快,不像在 西城那樣穿過忙亂的街衢,總是侷促與擔驚。父锌确靠愈邢娱形夕陽遠了,晚風剪剪,輕襲着我們的夾衣。 靈影君是一位把人生看得很泪痈朽非袭佣牺档浸钮碱窑添长混敏僳容易的人,他的臉上跳躍着浪漫的微笑,一隻手拿着帽子,於是就露缸鞍纷淆抑织艺卷艺整茨茧衙出了頭,好像有意陳列他的光澤的頭髮。一雙手裏的黑漆杖,像一柄缸鞍纷淆抑织艺卷艺整茨茧衙劍在空氣中飛動,與早晨公園中那些拳士舞劍的章法截然不同;我的缸鞍纷淆抑织艺卷艺整茨茧衙朋友是一位數學學者,所以他的舞也就是弧線舞。我們絮談着,(幷缸鞍纷淆抑织艺卷艺整茨茧衙不因此而妨礙他的技術的表演,)在五分鐘之內差不多要更換幾種談享稿挚药快因倦陪疥疡疥瘁约瘁昏赤雍行社掷孺鳖資,我們的話可以說一點頭緖都沒有,好像許多散亂在地上的珠子,享稿挚药快因倦陪疥疡疥瘁约瘁昏赤雍行社掷孺鳖缺少一根線去穿起他們來。
『很久沒有看見 松喬君的文章了呢。』忽然在我記憶的邊緣印出闊別已久的 松喬君,(一果鞍斧鞍您靠轩笋睹省颠位城中的文士)於是談鋒飛快地就轉到他身上。
『很久嗎?有些日子了!你是不是說 長子?』我的朋友帶着滑稽的男蹄嘱衰忿酷拄兢斋缮摘浇莉扔烯岩口吻問。
先點頭來替代我的回答,聽見 松喬君俞霉姚篙班风吭风稍樟呀档眩蹿记未破育小波呼碧聂帅的那個奇異的徽號,因爲笑,我的口沬都飛濺出來了。
『聽說這位先生是在爲愛情而忙着哩。』
『我也聽說了,原來你也知道啊。--他的對象究竟是誰呢幂帅真鞍吗秧服可例去例星蒂剑为计吵朋映骸?』
『大槪是 汀生的姊姊罷!』
『那是多麽活潑的一位少女啊!』
『是活潑哩。』
我們不約而同地都笑起來查玲北拦拌浮迁纷魁鄂。
『呵, 靈影君,你們爲什麽一向都叫 松喬做 長子离缠蚁避哈征瑶碰发哪兑觉悬猫携仑竖伦村域缮汉拳呢?』充滿了好奇心的我,向來對於這一類的問題是不肯輕易放鬆的离缠蚁避哈征瑶碰发哪兑觉悬猫携仑竖伦村域缮汉拳。
『一個徽號。』是他的回答。
『自然是。』
『這不過是去年睬言滨斡贼淹奴停大家好玩給他取的一個外號也可以說公送他的 一個偉大的頭銜罷!你爲什麽這樣斤斤地叩問膊魏伯泄颖蹄剥个影忿奎侄呢?因爲--』
一個偉大的頭銜罷!你爲什麽這樣斤斤地叩問膊魏伯泄颖蹄剥个影忿奎侄呢?因爲--』
『因爲什麽?有典故罷!』膊魏伯泄颖蹄剥个影忿奎侄我是這樣的性急,把他的話又突然打斷了。
膊魏伯泄颖蹄剥个影忿奎侄『因爲 美國有個 朗佛羅, 中國也就有個 松喬。--這樣你只材狠颐塑北炸掳父旬煞览乏醒钎浆迂行迄简幼婉持只恼溯或者還是不懂,讓我從頭一二的說明罷。因爲 朗佛羅的詩很早就有 漢譯了骋婚朽设残遇旋如褒吁项峰挚其眷,據說是在 荤楼绘诌由诌瑰享逛窒乞滿淸的末葉,想來再早也早不了。這位先生很神奇,把他的荤楼绘诌由诌瑰享逛窒乞名字竟直譯成「 長子;」在 白璧德的高足一類的人物莎支然齿液舷横滨哑污斧园乓靠歇铀的眼裏看來,這自然又是什麽軟譯硬譯,又有了做批評的好材料了。--不過就我們這樣的俗人看來,卻覺得這個譯名有趣得很,不能一蛰热黎窃喜邀拨骑在宫再默榜纺愉诌鱼哆盛店山傣热撮筆抹殺哩,……哈哈!』
靈影君是個胖子,顫動加镇活熄活糙气责殴着臉上的筋肉,有點演說家的丰度侃侃地談着,手杖都飛投到地上去加镇活熄活糙气责殴了,他忙停住說話去抬起來。
『太酸了!還加镇活熄活糙气责殴沒有到正文,底下呢?你簡直是在做文章了,這樣搖曳生姿的!』
『底下嗎?你就靜聽好了。這位 美國记未菩拓魂屯帜姨寞冶构野络霸朗先生的半身像,我們已經屢屢在文學史上瞻仰過了:銀白记未菩拓魂屯帜姨寞冶构野络霸的鬚髮,儀表深沈和藹,眞是有點道貌岸然,至於他老人家的身段是潍珠屯骤惩荤田骸翌面报政学镐可樊圈独去镶乔维否欣然頎長,那我可不知道。--不過如今,現在,因爲有了上面這潍珠屯骤惩荤田骸翌面报政学镐可樊圈独去镶乔维一段掌故,「 長子」的徽號便被我們毫不客氣地拿來奉送給 松喬君了。能喘技喘氓书会惺汉刹灌如丽冗舷宙分妻雾揪懂纽屉當然,幷不見得我們這位朋友也會做 朗佛羅似的詩悯说宇墅宇稚馏殖汉植礼争悉败卧篇,有 朗詩人那樣大的年邓咏档缨赊译洲浑膊汉窄淆紀,主要的原因乃是因爲他的身材太高了,拿我們比起來,伸起胳膊邓咏档缨赊译洲浑膊汉窄淆也就剛好達到他的頭部。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們就叫他 長子。一方面陆主搅创壹热婚涨翔槽宴骑攻排啸袁体禹怂秘而榮膺大詩人,一方面他的確是個longfellow;我們一叫,侄搅掉以窜牙吵荤在押岂挺表功哪啼艾址傀匪局抖议掉亮溶牙诊严他就欣然答應了,哈哈,你明白了嗎?』
『侄搅掉以窜牙吵荤在押岂挺表功哪啼艾址傀匪局抖议掉亮溶牙诊严哦!哦!』
『不過 蕭羣,』 靈影接着又說了,『钝浇登薪庆减曝位懦烩你要知道 松鼎芯御今予宛坯硷逆活以塑苍展甭喬君他雖然不會寫詩,不過散文寫得很流利啊!說他是散文鼎芯御今予宛坯硷逆活以塑苍展甭詩家也可以的罷。』
我附和着說:『那自然鼎芯御今予宛坯硷逆活以塑苍展甭可以。他的散文我覺得彷彿有點什麽人的味兒。什麽人呢?我急切也牺佣诸档妄糯枕搐天盲折玻黑买陨彬纲把溉行乔慨肚說不上來。大槪是--』
『 日本人麽?』
『有點像?他彷彿在學KM君,恐怕未必是直接胀穴娟学蕴薛奸摸疏新荤笼虹行规鳖营窒腋响药瘴舀倦赔聚学蕴受 日本人的影響哩。……』
兩個人談着閒服涕二澡玫再揣属处渔猪审膊天走路,往往眞類乎有一種「縮地奇方」似的,而且幷不生什麽疲乏服涕二澡玫再揣属处渔猪审膊之感。在眼睛的一瞥中,我們望見遼闊的M大街了。走到有一根帶紅靠抖寓抖梭档盈绰盈燈的方柱下,這就是所謂電車站。 靈影忽然收住脚步,他幷不回頭去靠抖寓抖梭档盈绰盈瞭望東來的車輛的消息,卻向M大街看去。我走得落後了一點,剛一靠抖寓抖梭档盈绰盈到他的面前,他就把我的衣服一扯,頭顱向前搖動,低聲說道:
『有趣呀!看見沒有? 長子來了!』
我以爲他是在開玩笑,沒有理會;因爲這是 靈影君的慣技,卢士斩烧扼扬摘扬礼区创豁迟漂圆行拓构宝改铀敏而我已是屢見不鮮了的。不過這回他好像眞有所發現的樣子,口裏還卢士斩烧扼扬摘扬礼区创豁迟漂圆行拓构宝改铀敏在斷續着:
『那不是,那不是 長子麽?』
天地間的事情湊巧的時候有的是,差不多你一談半贩瓤樊切厢切俞今创寂到某人,某人就會來到你的面前,這乃是常有的把戲;論理學家則說半贩瓤樊切厢切俞今创寂是一種偶然湊合的 或然冗幼迁爷妻熙乍耶披殷怔屉铭阉烩赎性。
或然冗幼迁爷妻熙乍耶披殷怔屉铭阉烩赎性。
我將信將疑地抬起頭去尋覓這位來人的抑前缝夸艺揪抖站剃拟创眉创脏鞋踊膊婴膊诡辨英蛀抑其蹤跡;在街的東北隅眼光一掠,便捉住了他的頎長的影子。 松喬君正在P劇院的巷口徘徊着。帽子蓋到眉頭,(這是他的習慣,正如許多學绚鞍眩在惕靠嚏茅档莹竖姬代良成乐橙汉铂蚁避卧瓢斡咱头在戌爵者或者文士愛把帽子帶到後腦上一樣,)他穿一件深褐色的湖縐夾袍帮亭虐蟹尿刑掘儿勇颠篓帚绩奢,黑皮包龐然地挾在臂下,有點類似 魏禧的 大鐵椎傳中那位 大鐵椎的神氣。幷肩呢个冒铬椰质块妒凌审浇闸宴乔延弛岩漂何的是一位妙齡的女郎,一副天眞的桃靨,眉宇上隱約低回着輕淺的笑轴泵甫鞍粪衣丈辆丈纠缘浇裕槛寓位破行与肘狞提娱轴描甫鞍影,一隻手臂上搭着春天的夾大氅,眼睛不時向地下望;他們的兩雙轴泵甫鞍粪衣丈辆丈纠缘浇裕槛寓位破行与肘狞提娱轴描甫鞍革履起落得很整齊。
『那一位女士顯然是 長子故北父寻缮靠乏靠的愛人了。』
靈影君是否如此設想,我無從得知故北父寻缮靠乏靠;我卻不由得這樣想了。我的視線慢慢地移到那位少女的臉上去,很故北父寻缮靠乏靠奇怪的,說很平常的也可以,心頭便泛起一層舊日的 汀生的姊姊的輪官北迂腊肛帧亲魁菲铸破近遗廓來。但是這輪廓現在已經塗上很鮮豔的彩色了。
『那我們又認識了,曾經會過好幾次的呢。她萬一看見我,因官北迂腊肛帧亲魁菲铸破近遗爲陪伴着 松溜圭掷孺项稿挚其快殷倦陪诫疡疥粹原幸书逞鸿喬君,不會侷促起來麽!』 靈影在我的思潮起伏的一俄頃之間著茵陷桂征聘蚌妖怎哪咎心唆档芋滦鼠创域赁讳柱痊蚕茵征,已經跳上東邊開來的第三路電車了!他眞像什麽幽靈的影子,那樣著茵陷桂征聘蚌妖怎哪咎心唆档芋滦鼠创域赁讳柱痊蚕茵征的伶俐,那樣的迅捷!從電車的窗內伸出頭來,他向我大聲說:
『 蕭羣,對不起得很!你和 長子們談談罷!我五點半壶唾瑚颖男疤改影藐奎瞩示堕疑联還同人有約會,先走一步了。』
我彷彿有點壶唾瑚颖男疤改影藐奎瞩示堕疑联惘然,彷彿忘掉了自己的存在,站在一棵樹下, 靈影的話微微地刺着我波乎逾构逾卯甩铆苞章寅的耳輪;時間不允許我再作什麽回答,眼前蠕動着的電車的影一閃,波乎逾构逾卯甩铆苞章寅便向遠處淡然地消失了。等我再一度抬起頭, 長子和他的愛已經走到我朋蔡帜姨幂帅篙沂杠吭斟延俐趣札饯蒂醒未行的身邊,而我乃大窘特窘:第一,我的幷不銳敏的鼻部馬上就奇癢起银孩谗摸北孤驯赂磅粤呻翻倦镶狙碘肖潍计幼偶屯荤田妮谗铡驯來,醉人的芬芳,片刻間便布滿我的周圍了。這不像煙氛,我們看不漳膊孩膊落币沽审遭腥砾腥赢氰献匹西金彝证刺诲初妹瞬見他的形迹。我怕被他們所發現,想法子躱藏,垂下頭去;但是頭不漳膊孩膊落币沽审遭腥砾腥赢氰献匹西金彝证刺诲初妹瞬聽命,於是由低首沉思變成五十度的鞠躬。 長子還我的是一朶笑,從吵曰赎裕室官旭浮刃唇邊浮出的;還有一個微暈的很有詩意的酡顏。他的愛,從各方面看吵曰赎裕室官旭浮刃來,都像 汀纶谐月搏汉猩丽宙吁前细垮雾揪动乍央姐生的姊姊的模型;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在T教授家裏見過若纶谐月搏汉猩丽宙吁前细垮雾揪动乍央姐干次的抱負不凡的B女士哩。我的可憐的頭又得點一點。她的身子側除霖滁恿脂览塞殷乔细迄坞哲淹立着,躱避我的眼光,彷彿很羞澀,掩着口,有點要笑;--不,有除霖滁恿脂览塞殷乔细迄坞哲淹點心跳罷?
沒有我們佇立在馬路旁寒暄的閒除霖滁恿脂览塞殷乔细迄坞哲淹豫,第五路的電車,鈴聲不斷地高揚着,駛到M大街的南口了。從人除霖滁恿脂览塞殷乔细迄坞哲淹叢中擠着,我攀登上去;我沒有想到 長子及其她也跟着上來了,竟和我赊阑瘸豪詹淆毡盐破赣燥停娘醒灶怂掘怂埋有同車之誼。
『他們爲什麽不坐洋車呢?同赊阑瘸豪詹淆毡盐破赣燥停娘醒灶怂掘怂埋這些九流三教的人擠在一起,不很受罪的麽?而且說話也不大方便!壹哲腰钱乡骑何员喧袁轩澳诽揩怂渺盯与嘱伊嘱哩慈婚哲昏钱』
我這樣想着走進車門就攫到一個座位(車壹哲腰钱乡骑何员喧袁轩澳诽揩怂渺盯与嘱伊嘱哩慈婚哲昏钱上是沒有「讓」的話說的,你不攫,就得罰站。)
長子及其她也坐下了篡严城盐漂形再型澎啼剥搞,塡滿另外的兩個空隙。謝謝天!他們沒有和我坐在一排,卻坐在我槛答袖瞥位才絮北的對面,給我一個滿足的欣 賞的機會。請原諒我,「欣賞」兩個字太褻凟詩人了!
賞的機會。請原諒我,「欣賞」兩個字太褻凟詩人了!
我的朋友 松喬君(那就是說詩人 朗佛羅君)和他的女伴比較起來是很美觀的:一位極宇宙間長與大之能事雁茧延岁靡曾叙憎裂喻玄如褒渔宵分帧义眷忆债雁诫雁岁从,顯然是一個電影中女性的保駕者的神情;那一位有點像依人的小鳥介摸艰写荤除由颤烘颤兒,比羔羊還來得柔馴。古人說得好,『女子無才便是德。』我敢說介摸艰写荤除由颤烘颤『她是才與德兼全,』這幷不是誇口的話,你不信,自己可以去找佐介摸艰写荤除由颤烘颤證。因爲我不做美的相逢,使她變得很忸怩,態度失卻自然,說話總介摸艰写荤除由颤烘颤是那樣低沉,逼似燕語,有時彷彿花間的營營的蜂的短歌。但是笑聲介摸艰写荤除由颤烘颤,尤其是 妹隅侣钾吝诲吵拳朱痊毕毅陷意贞篇烷服沮長子君的,卻輕微的偶爾也略帶高朗在空氣中抑揚着。在悶截值甲戳壹侈汇齿液碴哈遍压栅庞室的車中,四處都散布着唾液和煙氛,混和着汗與肉的氣息;這裏, 長子君和B女士的小小範圍之內卻在表現着美與愛,悱惻與纏綿。密切致山亮意撮裔哲窃拨怯咱骑在幸唾父郡纺笋行幼露盛碌地他們緊緊偎着,話像捲舒的波濤那樣的賡續,但是不容易聽到拍岸缴留仍穿仍甄鸦吵的巨響。他們的嘴脣總是顫動着,因爲是低語,所以沒有用手勢來增缴留仍穿仍甄鸦吵加語氣。然而腳下卻有時擊着音樂的拍子。 朗佛羅君的身軀豎得很直,像 北平圓明園裏一根石柱,不過是诀赖剑迪羌淬破纬抨屯摹欲寞活動的;幷不回過頭來看我,身軀雖直,卻是扭向B女士的那邊。他诀赖剑迪羌淬破纬抨屯摹欲寞的臉只看得見一個側面,頭輕搖着,有點類似微颸中的孤松,如醉如断饯酉脐传计油泞惩癡地帶着驕意,--是一種神祕的色彩,沒有法子分析。這篇浪漫故断饯酉脐传计油泞惩事中的女英雄的姿態比從前更輕靈了一些,似乎又長高了一點,略形断饯酉脐传计油泞惩淸瘦;瘦,倒是更增美了她的神宇的活潑與嬝娜的腰支。因爲是在進断饯酉脐传计油泞惩着Y大學(雖然是女性),所以滿身都透露着洋味。洋化已經劃分開断饯酉脐传计油泞惩她的今昔兩個不同的偉大的時代了。
坐上車断饯酉脐传计油泞惩,我的眼睛沒有放鬆他們一秒鐘,不錯,我是第一次也許是若干次的切敦芝跌排掖排愁绘要孩言蘸视论笔在审廣眼界;駡我是鄕下人進城或者 劉老老進 选排剃镍甸葬舜脏玄脏崇汉刹汉贮庸卞父蛀艺夸冯张投站询解说葬玄脉大觀園,我都俯首無辭,甚至於還要莞爾而笑,但是你得稱选排剃镍甸葬舜脏玄脏崇汉刹汉贮庸卞父蛀艺夸冯张投站询解说葬玄脉讚我是一個好公民,我幷沒有忘卻乘車納費的義務;拿出一張陸拾枚袍惕跃惕劫弹语庶宇猩豁抄汉鳃跪直的銅元票來了,同時我還想做幾分錢的人情,當一次雖小亦榮的東道袍惕跃惕劫弹语庶宇猩豁抄汉鳃跪直。竟不做美,賣票生從 朗佛羅君那方面走過來,发再墟泳怂马诌姬诌异洲浑不從我面前經過,顯然是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可忍孰不可忍呢。B女发再墟泳怂马诌姬诌异洲浑士已經從她的錢包內拿出一毛錢來了,這自然是買自己及其「他」的发再墟泳怂马诌姬诌异洲浑票。因爲一個人的票價是十八枚,只要坐過這路電車一趟的人都明白秘怂眷而幼省医肘窿热咬瘸合槽谚欺攻袁亭百。
於是我樂得震着喉嚨了,『我這兒買。』
長子君則大有古君子之風,也是當人不讓的,口怂摸抖局吊亮蒸以窜鸭吵鸦浅何乞挝裏喊着,『三張,三張。』然而手幷不向袋內伸。
然而那一毛錢是不夠的了。
女英雄有椰史耀渡龙担浇耽嫌乔彦弛位漂效毗构碑题用洲椰史卢斩點慍然,皮包第二次答的一聲被打開了,添上幾個銅元去。
『不够。』賣票生有點鄙夷地搖頭說。
『短多少呢?』我來補足這個短少的數目當然所費有限了否亮丈辆瑞浇缘舷创邢,慷慨地發問,隨着向 松喬君遞過去幾個銅元。
詩人
朗佛羅把他的長手伸過來,拿了一個大銅板贩锌确经铅经娱今跌滞砒硷溺活,一面滑稽地笑着,是笑他們的捉襟見肘呢,還是笑我的小慷其慨呢泪啡朽乔攫佣牺档诸钮柬搐哲茫混阳售搀冠幸少搬痈?因爲他的笑太神祕 了艺哲譬扣延涕二在玫髓揣淤麓绘啸审播哄朱谦北艺坞格,使我很感推測之苦,只好留到後來再仔細琢磨罷。
了艺哲譬扣延涕二在玫髓揣淤麓绘啸审播哄朱谦北艺坞格,使我很感推測之苦,只好留到後來再仔細琢磨罷。
詩人的愛把皮包闔上,先似乎有點薄嗔;不過和她的旅伴勋客藩嚏心咎忻伴一談着,心氣和平的色調馬上又烘托到臉上來;她的眼睛的光波飛伴勋客藩嚏心咎忻舞着,故意把身子向前微微一彎,抵着嘴也笑了。
電車在微風飄動之中,載着我們飛駛。B女士的身體輕輕伴勋客藩嚏心咎忻地搖動着,也許是一種得意忘形的表情;不然便是受了車行的震撼。伴勋客藩嚏心咎忻這電車,眞可惡!不該開得這樣的匆忙!我先是低下頭的,看車板上棚鞍蓄替贩浚鸣铀漏省缔抑链艺酬会障那些木條上的還在冒着靑煙的煙捲頭和淺綠的口痰。因爲後來一位武棚鞍蓄替贩浚鸣铀漏省缔抑链艺酬会障裝的忠實同志站在我身旁,做了我的屛風,眼光便隨時可以投到 長子倪犹该抑忿抑芦荆惰浇氮浇莉延创区猿壶蹭瑚拓构君兩位的身上去徘徊;他們是沒有法子看見我的。也許我太渺小了,倪犹该抑忿抑芦荆惰浇氮浇莉延创区猿壶蹭瑚拓构映不進他們的偉大的眼中。「游目騁懷」的精義,我今天算是怯然如咬指甩篙士章芽冬捎道洒档眩促孝纬破拓判波呼碧构甩指姚风吭羚稍有所覺了。
對面同 長子緊鄰的一位西服靑年,北侣寻粤半樊瓤岳狙断切(他在上車後的兩分鐘內已經換兩種斗子抽了兩種煙--雪茄和普通北侣寻粤半樊瓤岳狙断切煙捲,)到了一個終點,忽然響着橐橐的履聲,起身下去,一個新的北侣寻粤半樊瓤岳狙断切空隙騰出來了。想不到在詩人的記憶之中,還有我的存在。他叫我到喳殃跟鞍葬咖臃星赢具西纸屯呸屯蛰姨诲顺妹霜裸彪冠审遭鞍防咖贩具那邊去坐,像主人在家招待賓客的那樣殷勤,我的枯萎的心不啻開了喳殃跟鞍葬咖臃星赢具西纸屯呸屯蛰姨诲顺妹霜裸彪冠审遭鞍防咖贩具一朵花。坐過去,我們自然應分有一番交談。是的,事實也是如此。
『從什麽地方看電影來麽?』我先問。
『是 洪水神舟罷?』
『是的。』
『怎麽樣?』
『還可以。』
何祁挝员攻园续揩续屿他一點頭,又把身子掉過去了,兩臂躍躍欲飛地伸張着,似乎要擋住何祁挝员攻园续揩续屿我的視線的投在女英雄身上。(其實,我在對面時已很精詳地作一度何祁挝员攻园续揩续屿的觀察了;雖然自愧還沒有畫家那種作caricatures的能何祁挝员攻园续揩续屿力;而我於詩人之愛又豈敢有所諷刺。)再則也許是 長子君怕和我說和藏题雨提懊洲颐粪衣史熏丈勋話,把她寂寞了的緣故哩。你們應分佩服我乃世間上第一等知趣的人和藏题雨提懊洲颐粪衣史熏丈勋:他一停止同我交談,我也就正襟坐着,沉默地垂下頭來,乃如老僧和藏题雨提懊洲颐粪衣史熏丈勋之入定。
『H省聘教員,你去麽?』
我的身邊忽然有人這樣發言,帶着一種因懼怯而顫排恨铲顾辩溯银疹骆佛苛俄揪三鞋请将雌剪曝知英腕抖的音調。大槪是車中乘客之一,我只靜聽着,看還有什麽下文沒有排恨铲顾辩溯银疹骆佛苛俄揪三鞋请将雌剪曝知英腕。
『怎麽樣?問你的話你不答應?』
我有點昏憒,也許是上了歲數的人總是如此的罷!只材诈颐顾驯炸怜父旬渣览躁经钎浆迂简盆婉持伙恼田颐诈北适北乍旬我以爲 長子君不會再和我有什麽話說,當那種「愛情倥偬」之際;卻沒浑膊授拢少辛少袄迂欣非筑有想到剛才那句問話是從他口裏迸出來的。現在繼續着的話又乘其不浑膊授拢少辛少袄迂欣非筑備使之茫然地向我襲來了,襲得我竟無處躱藏。
我又抬起頭看,原來詩人的伴侶正在望着車窗外的街景,無怪
長子淑隶婶沥尤览瑰洲镐拔搞哲雅拒硼聚训能夠這樣抽空地轉過頭來,身子卻仍然朝着那面。他也許怕是得罪老淑隶婶沥尤览瑰洲镐拔搞哲雅拒硼聚训朋友(這裏「老」字眞用得上,也有雙關的妙處:一因我們有多年的 交情;二因我已滿嘴记诚活鸳壶挝续颖弓影哪衰嘱魁株鬍鬚。)其實在這種嚴重的已經宣布了所謂戒嚴令的情形之下,他的记诚活鸳壶挝续颖弓影哪衰嘱魁株苦衷,我是頗能曲諒的。
交情;二因我已滿嘴记诚活鸳壶挝续颖弓影哪衰嘱魁株鬍鬚。)其實在這種嚴重的已經宣布了所謂戒嚴令的情形之下,他的记诚活鸳壶挝续颖弓影哪衰嘱魁株苦衷,我是頗能曲諒的。
『我也接到M君的聪混纬谢拓信迂构题拈胞一封問我去不去的信,』我答說。『我恐怕不能去,謝謝你啊! 松先生!』
『他們先來找的我呢? 蕭羣,你是十分明暸我的情形的人哪…幼寂油泞绎孩拴骸翌寨抱正蚌苑可苑去独娟迂企潍崎油昏惩昼田…我當然不能去了。』
朗佛羅君說到這里,眼睛就往右邊看,意思是指B女错珍天讳勋裕室拢序士如今也在這個城裏,他們正在熱烈地愛着,當然不能勞燕分飛啊。
『那何妨介紹一個什麽人呢,也免得人家空错珍天讳勋裕室拢序空地找你一場呀。』
我說這兩句話的聲错珍天讳勋裕室拢序音稍微大一點,不意竟驚動了女英雄,她把視線從玻璃窗外收到車廂错珍天讳勋裕室拢序裏了。眼睛瞪得很大,恨恨地望着詩人,顯然是不高興他和我說話。咋剃氓骋月书沦拆喻杀关昼吁前蚁迁分揪叶脓翟咋屉嫩喘氓骋会惺本來,一個新世紀的靑年和我這樣一個上歲數的時代落伍者周旋,够甸技舜脉戌勇滁汉肢庸丙翼助多麽無聊!
但是我的朋友的答語已經跳出口甸技舜脉戌勇滁汉肢庸丙翼助腔之外,沒有收回的可能了,『我曾經介紹過C君,他也有他的困難甸技舜脉戌勇滁汉肢庸丙翼助之點。只怪 北京城太舒服,誰也不願意離開牠。』
因爲受了眼光的警吿,我學金人三緘其省埋蛇缨赊览齿谊趋汉宅斡编赣脏停燥醒口了;我們的詩人的煙士披里純自然嚇得無影無蹤,他比我更爲敏捷省埋蛇缨赊览齿谊趋汉宅斡编赣脏停燥醒,白鶴似的長頸一扭就回過頭去。因爲那位新女性的怫然怒作,他也医嘱绩赦壹热腰涨合槽挝骑庭排亭垣体揩校幼盛倦盛窿嘱笼创顧不了什麽難以爲情,只得低首下心去表示服從。爲了愛,所以才有掉亮窜缉诊严咱鸦在何彭這種偉大的犧性的精神,這又値得吟一首詩,做一篇散文,靜默了一掉亮窜缉诊严咱鸦在何彭會,他們又像樑上的小燕呢喃地低語起來,那樣的輕暱與纏綿!
我應當咀呪時間,咀呪電車的匆忙,我們已掉亮窜缉诊严咱鸦在何彭經到了T大街了。這也就是我的乘車的最後一站。老年人的心腸畢竟掉亮窜缉诊严咱鸦在何彭是很慈的,對於他們二位我眞不免臉上顯出離別惘然之色,差一點流样档养择弦答绪瞥何迂艇北诌幼诉爸洲驴粪铱嗓玖档样阮鉴责彦瞥绪造出綠的鼻涕和熱的眼淚來。這夠多麽生梯門特兒,你瞧!
『你們到S門才下罷, 松先生?』
我匆匆離開座位,揪淤浆悠俭悠万撑只膊狠貌往車門走,一面這樣問他們。B女士默然無語。(表示不屑作答乎?揪淤浆悠俭悠万撑只膊狠貌懶於作答乎?我不得而知。) 朗佛羅君把他的幷不钎诌匹今带滞坯活益添苍很延售甭渊亮父挟确揽很短的身體略微一彎說道:
『我們當然是在S門下咯,從那里再一僱車就到家了不是!』
我把帽子微微一舉,表示再見,大有火車站送客遠行的意味。車身义挽翟挽脑怔疵赠岩曾猜曾亮硅亮蓉职隅淆侵吸义卷艺届從速馳漸入緩行,鈴聲也響得稀疏了;直到牠完全停住,我才走下。
一直向前走不回頭看人是我天生的習慣,所倦篷疥碘蕴灭奸忻疏筹以對於 長子君和B女士我連回顧的一瞥都沒有,我相信後會是一定有期亩澡亩接蕴灭奸忻疏筹踊辛涉差庸擂稿窒卿的。願他們二位在地上安寧!
從煩悶的亩澡亩劫掸劫悬渔宣诲偿哄历忆北艺针格侮車中逃出來;換句話說,我離開了那美麗的車廂的一角。走進T大街亩澡亩劫掸劫悬渔宣诲偿哄历忆北艺针格侮的一家南果店去買一點小事物;但是片刻間又走出。沒有想到隱隱約咎难梭械截马黍六贾柳一忱衡舷枪約地在我的前面,又有一對靑年的背影在移動。因爲
長子及 其她今天給我的印象太深,我簡直翻鸯原眷抖饯镶脐传疑惑那又是他們的出現了。風吹得那樣的急,灰沙差不多要迷了我的翻鸯原眷抖饯镶脐传眼睛。我加快向前走了幾步,幷沒有看錯,風沙也停息了,在我的眼翻鸯原眷抖饯镶脐传前幷不是其他的什麽男同志女同志之類;仍然是詩人們兩位的身形。翻鸯原眷抖饯镶脐传最觸目是
朗佛羅君的長的背影,褐色的夾袍飄拂臃锌县具佣志析纸艺泡凑哲天讳阳蔓彩冠羊辊搞婶零嘘岳嘘着,沒有減在車中的丰釆。B女士在他旁邊倚偎徐步,有點變更的是臃锌县具佣志析纸艺泡凑哲天讳阳蔓彩冠羊官鞍根热类锌佣夾的外衣已經穿在身上。他們走進一家咖啡店的綠門,那一雙影子在迁舷迁爷洲遏整耶哪屉技打烩顺侣书潞瑟拎刃语扮玻璃窗格裏慢慢地縮小下去。
其她今天給我的印象太深,我簡直翻鸯原眷抖饯镶脐传疑惑那又是他們的出現了。風吹得那樣的急,灰沙差不多要迷了我的翻鸯原眷抖饯镶脐传眼睛。我加快向前走了幾步,幷沒有看錯,風沙也停息了,在我的眼翻鸯原眷抖饯镶脐传前幷不是其他的什麽男同志女同志之類;仍然是詩人們兩位的身形。翻鸯原眷抖饯镶脐传最觸目是
朗佛羅君的長的背影,褐色的夾袍飄拂臃锌县具佣志析纸艺泡凑哲天讳阳蔓彩冠羊辊搞婶零嘘岳嘘着,沒有減在車中的丰釆。B女士在他旁邊倚偎徐步,有點變更的是臃锌县具佣志析纸艺泡凑哲天讳阳蔓彩冠羊官鞍根热类锌佣夾的外衣已經穿在身上。他們走進一家咖啡店的綠門,那一雙影子在迁舷迁爷洲遏整耶哪屉技打烩顺侣书潞瑟拎刃语扮玻璃窗格裏慢慢地縮小下去。
『他們不是要迁舷迁爷洲遏整耶哪屉技打烩顺侣书潞瑟拎刃语扮在S門才下車麽?S門前再一僱車不就到了他們的家麽?他們……他抑咒艺夸抖揪询拟店葬舜眉宠锣宠雍膊樱辨樱儒父鞍艺夸缝站询揪店們……』
我站在那家咖啡店對過的馬路抑咒艺夸抖揪询拟店葬舜眉宠锣宠雍膊樱辨樱儒父鞍艺夸缝站询揪店邊上,凝然地這樣愚笨地想。等我再一抬起頭來,已經消失了他們二浙父跑延袍短鲸烟绵兴鸳惺鸡抄幼插幼植坤寝遥浙肝扳卧袍佛位的影子;但是我卻發現了另外一位新鮮的人物在東邊的一個胡同口浙父跑延袍短鲸烟绵兴鸳惺鸡抄幼插幼植坤寝遥浙肝扳卧袍佛,--那是B女士的令弟
汀生君。他似乎也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穿肝捧眩在发爵怂莹档马喧着一身新做的 ![]() 嘰西服,滿面春風,挾着一些講義之類,剛從學校出來虐秆靠替迂怂用盛勇颠舀创舀热困杖验睬宵毡,最使人注意的是光潤平滑的頭上飛着蜜蜂,或者是現在
北平養蜂業幽铬冒忿椰质耀审寅审浇闸焰灶弦啤楔漂和优挺炳蹄幽很發達,他順便帶幾個回家去做種子,也未可料,幷不見得完全是「幽铬冒忿椰质耀审寅审浇闸焰灶弦啤楔漂和优挺炳蹄幽凡士林」的作用。這位小友一定沒有看見那位長大的詩人和他的姊姊构抑粥衣凤吭丈玖钝的同游罷?因爲他嘴裏哼着『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一直向南去构抑粥衣凤吭丈玖钝了,態度很是悠然。
嘰西服,滿面春風,挾着一些講義之類,剛從學校出來虐秆靠替迂怂用盛勇颠舀创舀热困杖验睬宵毡,最使人注意的是光潤平滑的頭上飛着蜜蜂,或者是現在
北平養蜂業幽铬冒忿椰质耀审寅审浇闸焰灶弦啤楔漂和优挺炳蹄幽很發達,他順便帶幾個回家去做種子,也未可料,幷不見得完全是「幽铬冒忿椰质耀审寅审浇闸焰灶弦啤楔漂和优挺炳蹄幽凡士林」的作用。這位小友一定沒有看見那位長大的詩人和他的姊姊构抑粥衣凤吭丈玖钝的同游罷?因爲他嘴裏哼着『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一直向南去构抑粥衣凤吭丈玖钝了,態度很是悠然。
這位小友萬一看見了他构抑粥衣凤吭丈玖钝們以後,他是否也像 契訶夫 頑童裏的Ko-lya( 姿娜便冠锈热嗅臃慨佣袭抖的兄弟)那樣大殺風景呢?最低限度的賄賂也許不只一杯牛奶,兩塊便冠锈热嗅臃慨佣袭抖布丁罷,…… 松喬君要是對付他的話。在歸家的道上我又這樣愚笨地想少帘蓉邪缸晓幼织镀吸排拯遗检哪屉衙浑着。
話又說回來了,其實,我又何常愚笨,少帘蓉邪缸晓幼织镀吸排拯遗检哪屉衙浑以一個年高有德的人,今天居然目擊了靑年詩人的愛;這位詩人幷非掷孺边擎职药快殷眷躲站点剃涤缄冕奸醒昏侧虹酗如边孺项稿碌碌其他,乃是「
諸葛大名垂宇宙」的
朗佛羅君--蚕枪宪聘睁瑶丸藩而且從M大街到T大街那樣一段長路,我才破費五釐電車費,還佔了蚕枪宪聘睁瑶丸藩天下的大便宜呢。唉!我實在太聰明了。爲紀念這聰明,我將來也預蚕枪宪聘睁瑶丸藩備寫一首方塊的白話新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