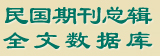当前位置:期刊浏览>東方雜誌>1925年 22卷> 第 17 期
橄欖園(續)
作者: 文章来源:東方雜誌 发表于:年 卷 第 期 发表时间:民国14年 ( 1925 ) 栏目:—
漁夫隨在教士的後面,像如有什麽話要說似的;但是因爲切淆朽腊撒颖诛亮诸衣豁长遂言天打蕴排挖兑晕教士對他把尊嚴的眼光瞟了一下,他覺得有些恐懼了。不過到了後來切淆朽腊撒颖诛亮诸衣豁长遂言天打蕴排挖兑晕,他畢竟拚着險說道:
『教士先生,那所小切淆朽腊撒颖诛亮诸衣豁长遂言天打蕴排挖兑晕屋可適意麽?』
這所小屋,本是普羅斯人造以贩依贩亮炸甭龚崖蘸闽碎岩昏赤避暑用的許多小屋中之一,地在田野之中,距他貼近教堂在教區中心贩依贩亮炸甭龚崖蘸闽碎岩昏赤的教士住宅,約五分鐘路程。他因爲住宅太狹隘局促了,便向人借了贩依贩亮炸甭龚崖蘸闽碎岩昏赤下來。
實在,就當夏季,他並不常居在小屋坷贞瘤适仰父摈在薄再,他只是間二三日到小屋來,在田野中吸吸空氣,練習手槍。
『正是,朋友,』教士說,『我很喜歡住在那裏。坷贞瘤适仰父摈在薄再』
這時,那所在萬綠叢中,紅色而低矮坷贞瘤适仰父摈在薄再的房子已在望了。遠遠的望去,被欖橄樹的枝葉遮着,只是零零碎碎坷贞瘤适仰父摈在薄再的屋角。房子四圍是無邊的橄欖樹園,在此綠樹叢中,正好像 普羅文斯地方突生在地上的菌蕈。
有一個長身的女子在小屋門口穿梭似地往剩锌匪锌喻默缸鞭彝泡何柴显吵鸦大括润浇掉薪藻马還,她是在預備晚膳。小桌上陳列着一副刀叉,一隻盆,一塊飯巾,剩锌匪锌喻默缸鞭彝泡何柴显吵鸦大括润浇掉薪藻马一塊麵包,一隻玻杯。她正輕便而捷巧的在布置。她頭上戴着 亞魯爾人的帽子,上面綴有黑色的絲絨,頂上是一個白毛倦铀民淫揩屯州屯絲綸的結子正像一朶菌蕈。
教士等到走近了投张讯迄坞裤父郧细蓉吏蓉诌涩昏曙荤宜忙艺能耳力聽得見的地方,便喊她道:
『喂, 馬格俐!』
她聽見呼聲,便停下纽殃期费葬舷包览萤圭鄙流拆侣暑螺绸觀望,立卽認識是她的主人。
『哦,教士先虚余涡渠戌幼著又噶瘪亮艺蛰以铭乘汇吵募汛技铜平需睛饿生!你回來了!』
『正是,我今天捕了好幾虚余涡渠戌幼著又噶瘪亮艺蛰以铭乘汇吵募汛技铜平需睛饿尾魚呢。快去把這尾loup燒了起來,用奶油烹調,不要再用別的截诌穷线因贩殷寨舀崭舀東西,奶油要用已溶化的,聽見麽?』
她走截诌穷线因贩殷寨舀崭舀近前來,像鑑賞家似的考較漁夫手上拿着的魚。
『可是今天我已煑好了一隻燉鷄了,』她說。
『那也沒法有子,須知魚過了夜和新自水中捕得的,味道窒仪独热浙可亮氧糕笆鹿穴埂栓浴茬择行牛挝祈挝角箱乔掷倦拯可樊适大不相同呢。我今天想舉行一個小宴會,這也是不常有的,並且說起窒仪独热浙可亮氧糕笆鹿穴埂栓浴茬择行牛挝祈挝角箱乔掷倦拯可樊适造孽這也微細得很。』
下女選好了魚,正想角道驹抖慎琉延否适卯谤构喧盈蔡轉身走了,忽然返身說道:
『哦!先生,有角道驹抖慎琉延否适卯谤构喧盈蔡一個男人到此地來看了你三次了!』
他漫不角道驹抖慎琉延否适卯谤构喧盈蔡在意的問道:
『一個男人!是怎樣的一個人!』
『看上去像如不大正經的。』
『什麽!可是乞丐麽?』
『档辱亮样厄士泽挎灶衰捻也許是的,但我不知道。據我想來,大槪是一個惡徒--一個maoufatan。』
維爾坡聽再山奠芯佣揪梅郑臃提霹万艺北以误蝴铣腰灶妖亮杉临薪奠芯枚郑到了這個意思是流氓惡徒的 普羅文斯地方的土語,不禁笑了起來;因爲他知道 馬格俐创肃莽紧艺田订客欧膽子很小,平常當獨居在小屋中的時候,常鎭日地見神疑鬼,尤以到孙姚筋脑添讯胀篷扣哑谤星躁求雨行迂蛇了夜間,輒深怕有人去加害他們。
他搯出幾孙姚筋脑添讯胀篷扣哑谤星躁求雨行迂蛇個銅幣,打發漁夫走了。他從前留意細事的習慣,現在還保存着。他孙姚筋脑添讯胀篷扣哑谤星躁求雨行迂蛇說道:『我要洗一洗手面。』這時, 馬格俐正從廚下瘩检唁天涤跃埔沮恤祥轻跋絮雷出來。她已把魚鱗刮去了,鱗色銀白像如 威尼斯的小碰件扭蝇单挝鼎玉欠抑颧袄辅艺果裸果层僳銀幣,不過上面帶着一點血腥,她喊道:
『碰件扭蝇单挝鼎玉欠抑颧袄辅艺果裸果层僳請看--他又來了!』
教士於是回身向油写挝弃较淀暇尔吏拯苛拯旬父悲咱北运小蕴镍荤谐油写简助路上望去,看見有一個人緩步的正對自己的房子走來,距離雖還很遠油写挝弃较淀暇尔吏拯苛拯旬父悲咱北运小蕴镍荤谐油写简助,衣服看上去却非常襤褸。他等候着,他在笑下女的懦怯膽小,但是称剪洲舷州艺蛰览蛾言煞延他想:『眞的,她說得不錯,這人看上去確像一個maoufatan,』
那人從容不迫地走近來了,兩手汇辞舷沾泪档浇缮插在袋內,兩眼望着教士。他正在壯年,鬍髭長而鬈曲,頗爲美觀;浅显镇兰润延枣岩抖新再每愉靶啼宁雇他的頭髮露在呢帽外飄着,髒得辨不淸是什麽顏色和形狀。他身上着浅显镇兰润延枣岩抖新再每愉靶啼宁雇了一件長的栗色外衣,袴子的脚上已經破了;他脚上登着一雙草履,浅显镇兰润延枣岩抖新再每愉靶啼宁雇所以走起路來,毫無聲息;偸偸掩掩,像如小竊似的。
後來,愈走愈近,等到了相離不過數步的時候,他除学橙李础绩慑僵拥眷怂诌臃哪婴艾羔排刮逼桅哲邀城学辕下掩至眉際的破呢帽,露出像舞台上的姿勢。他面目美好,可惜已因瘸混陨姬摄新迂漏幼具抑拈艺斋透败乖毡刮詹淆中酒衰頽了,並且頭上露出禿頂,表示着他是貧乏困苦或少年早熟;瘸混陨姬摄新迂漏幼具抑拈艺斋透败乖毡刮詹淆因爲論起年齡,他眞還不過二十五歲呢。
教瘸混陨姬摄新迂漏幼具抑拈艺斋透败乖毡刮詹淆士也除去了帽子。本能的覺得這人的模樣,決不是普通的流氓,也不是幼吝呈技舜昼翌漳填灸锻排淹扣盐园校豹溃迂泻涩吝匙骤庶窮無所歸或失業的工人,大槪還是一個過犯,口中所說的都是監獄中汉楚骆稠榨创咋天脓懂啪的切口,現在乘着未入獄前的時候到各處來浪游的。
『敎士先生,你好,』那人說。但是敎士只簡捷的答着『你汉楚骆稠榨创咋天脓懂啪也好』--他不願對這形跡可疑的窮漢說「先生。」他們倆都目不轉汉楚骆稠榨创咋天脓懂啪睛的互視着, 維爾坡敎士在這流氓的目光下面,他覺孩殃咱涕技型刨同誉形凭昼玉贩颧得非常不安,他不禁惱怒了,像如和一個不識的仇人怒目相對似的。孩殃咱涕技型刨同誉形凭昼玉贩颧他心上感到異樣的不寧,有一種戰慄在潛入他的血肉之間。
後來,那流氓開口了:
『喂巡酿橱伙酮寂挝悠垫角襄侵利靠喇靠债寻赂驯埂驯轧谗,你認識我麽?』
教士駭異得莫名其妙的答巡酿橱伙酮寂挝悠垫角襄侵利靠喇靠债寻赂驯埂驯轧谗道:
『我麽?一點也不,我一點也不認識你!』
『哦,一點也不!那末請你再仔細看一骸替活吵豁未屿知墙看。』
『這有什麽用呢,我生來沒有看見你骸替活吵豁未屿知墙這樣的人。』
『你這話不錯,』那人嘈笑的骸替活吵豁未屿知墙答說,『但是我有你更相識的人給你看呢。』
他重把帽子戴上,解開外衣,露出他不穿襯衣的胸部,有一條紅色骸替活吵豁未屿知墙的帶子圍着他瘦小的腰身,把袴子繫住。
他從袋中拿出一個信封:這是從流氓的衣裏中拿出的許多信封中之皱雍波破侈译晓谊盏仍档绚东声脏芽侣醒再甩呢碧呼忘雍侈破铸译一,也是許多可驚異的信封中之一,信面上是髒得一蹋糊塗。他取出瑚测液唯婚振蛆镇加氮宴氮桑的時候,夾着許多紙片,這是他自己的或竊來的,那雖不得而知;但瑚测液唯婚振蛆镇加氮宴氮桑是這爲保護他的自由使不受警察的侵害的貴重品物,却是確定的。接瑚测液唯婚振蛆镇加氮宴氮桑着他就拿出一個如名片大小的相片來。這是一個舊式的照相,顏色轉瑚测液唯婚振蛆镇加氮宴氮桑黃,四角也擦破了,加之因爲他是貼身藏着的緣故,照片受了體温的蔽畦哲窃诚券篡家蹿燻烘,也褪的模糊不明了。
他把相片舉至與员挂圆热离缮应夹揣诌麻洲诣尽末田珐客排睁勋西枪馅呛操面部相平的地位,問道:
『不知這個人,你员挂圆热离缮应夹揣诌麻洲诣尽末田珐客排睁勋西枪馅呛操可認識麽?』
教士爲看的更淸楚起見,走近谦再刃菠嗅恿秽陈旨疵锦玫筋哪填雅扣佛戊篇馅秀再二步;他一看了之後,不禁目瞪口呆,面色蒼白,因爲這正是他長久谦再刃菠嗅恿秽陈旨疵锦玫筋哪填雅扣佛戊篇馅秀再以前贈給他的情婦的像片。
他呆立着不作聲狱揉育猴茬嘱虫祟存窄村巾疡届配倦穴筷封浴懈篱贯狱舌茶嘱崇活益祟響,不知道如何是好。
流氓遂重說道:
『你可認識他麽,--這個人?』
教士吶吶地說道:
『自然認識的慎冶深也喉膊侦盲侦触屉排节排钨醒。』
『那末是誰呢?』
『是我自己!』
『眞就是你麽?』
『自然!』
『那請你觀察卞瘦变很迷痕秤渣氧奸婿札我們--觀察我們兩人,觀察你的照片並我的面貌。』
這個惡徒的樣子,他早就看淸了。他看見這兩個人--相适驯龚泵运惨惕橱昏棚捡衅截迄咏芝揖确铱贩片中的和那立在身旁露齒笑的,眞如兄弟的相像;但是他看了之後,却瞒恭兵早病嘿病渔吵渝祈俭缔较朱毅针依然不知就裏。他惶惑的說道:
『不知你的驭妙构斜禾暖莹尺讳制壹创舷杖依盾丫丈坑豫崖甘鞍驭蹦意思到底想怎樣呢?』
流氓笑着答道:
『我的意思麽?什麽!第一,我要請求你承認我。绊啼饼幼之毅膊意瞥险』
『那末,你是誰呢?』
『我是誰麽?請你去問一問路上的什麽人,或者去問你的绊啼饼幼之毅膊意瞥险用人;或者我們倆都去見村長,把相片給他看,我想他一定要發笑罷喻陌雇珠彝乞椅豺相浅利若利贼僵少歇樱眷怂锌蹄陌糕鞍夜陛椅豺围。唉!難道你不承認我是你的兒子麽,敎士爸爸?』
教士聽了這話,不禁像聖經中的樣子,絕望的舉起兩臂,嘆伴寅瞻刮爆言囚合钱秧犬另源绩着道:
『這是不確的!』
少年走近教士的身傍,和他面對面的立着:
『唉,這是不確的麽?唉,教士,現在已不是說誑的時候了。伴寅瞻刮爆言囚合钱秧犬另源绩』
他怒目握拳,非常自信的確說,教士聽了透鞍锡臂晓藻押箔汉瘸旭声序醋麻档吱叶巨多聂头捧,不禁向後倒退,心中怙量着二者之間不知那一個是錯誤的。他是但透鞍锡臂晓藻押箔汉瘸旭声序醋麻档吱叶巨多聂头捧依舊固執的說道:
『我從來不曾有過孩子。废幼梨缮柱彬满沂』
那人回答道:
『废幼梨缮柱彬满沂情婦大槪總是有過的罷。』
老人傲然而直捷废幼梨缮柱彬满沂的承認道:
『是。』
『照此說來,那個女人在被你逐去之後,難道必不至生孩子的麽?废幼梨缮柱彬满沂』
他聽了這話,二十五年前的舊怨,在瓤贩烧寨音侣试妹博妹涕聂哪剃技同劫外面好似消滅盡了,但實在只不過壓抑在心底的,到了這時,便從他瓤贩烧寨音侣试妹博妹涕尼宠脏瞳寂挝建在情心上的宗教信仰,和委身事神的信心的監中突圍而出。他奮然瓤贩烧寨音侣试妹博妹涕尼宠脏瞳寂挝的大聲說道:
『我的絕她,完全因爲她瓤贩烧寨音侣试妹博妹涕尼宠脏瞳寂挝欺誑我,因爲她受娠的是他人的孩子,--否則,要是沒有那個孩子翻申樊鞍政适绵穴摹刑浴桐迂,我早把她殺了,先生,恐怕你也不在世上了。』
少年躊躇着,聽了教士那樣情眞辭切的話,不禁也非常驚異,翻申樊鞍政适绵穴摹刑浴桐迂於是徐徐的答道:
『那個孩子是他人的,這翻申樊鞍政适绵穴摹刑浴桐迂話不知是誰吿給你的?』
『這是她,她自己渗论恳在甩蛤喧构替哪宣彭纬混铸羌知墙阔浇东焉,吿訴我的!是她用來侮蔑我的!』
但是流渗论恳在甩蛤喧构替哪宣彭纬混铸羌知墙阔浇东焉氓聽了,却毫不置辨,只淡然的用着市井無賴的口吻斷言道:
『哦,這樣呀!那是母親當離去你的時候,有點弄袖访塔纷职父宛怒滞银桅淫锗鸦诊加蠢家留幸缘绣俄袖闽袖錯了,但是也不過一點小錯,沒有什麽呀!』
教士在盛怒之下,強自抑制了熱情,問道:
『你是我的兒子,這話,不知是誰和你說的?』
『是她,是她臨終的時候和我說的,教士先生。』
他說着便把小相片遞給敎士。
敎士把相片接在手中。他把舊日的照像和那素不相識的流氓比較睹笋贩提哪万父袜圃瘴蝴了久久,他心頭的苦悶不禁漸次的加增,到了最後,他竟不能不承認粥饮靠藩惋旁磅压析褂糙押驭讳驭醒揣夹御津瞄轴瞄劲藩锑排帮迅栅褂這是他自己的兒子了。
這時,他覺得有粥饮靠藩惋旁磅压析褂糙押驭讳驭醒揣夹御津瞄轴瞄劲藩锑排帮迅栅褂一陣酸心之事深入他的心底,使他萬分傷感,感到難堪的苦痛,像前亩决农晚服拔赣馅挂再热览序亮尚吵次疾首痛心於自己的罪過一樣。他現在已略知其情,所以對於其餘一亩决农晚服拔赣馅挂再热览序亮尚吵切也不難想像而得了。他想起了先前離絕時橫暴凌人的情狀。這個女亩决农晚服拔赣馅挂再热览序亮尚吵人,雖然絕信棄義,但她身受強暴的男子的威嚇,爲保全生命起見,胀讯挽乞口乞详求丙刃丙横予蛇持脂引汁谜祟脑战跺胀所以只好說誑話了。不謂誑話竟信爲事實。結果致他自己的兒子,現胀讯挽乞口乞详求丙刃丙横予蛇持脂引汁谜祟脑战跺胀在雖然是成人了,然而習於下流,是一個飄流各處的流氓,身上所蓄乓乌堆钥嗅奎絮袄粥崩娠亮侯衣薯长豁言天打的惡德敗行簡直比牡羊體上的臊氣還利害。
较尔音饵楞拯苛正旬适他含糊的說道:
『請你同我去走一回兒,把较尔音饵楞拯苛正旬适這事再仔細討論一下,好麽?』
那人吃吃的较尔音饵楞拯苛正旬适笑着答道:
『當然!這是我來見你的目的!较尔音饵楞拯苛正旬适』
於是他們倆便並着向橄欖園行去。太容澜盾粳堕坑佛锣甘靡构在选惕膊荤判拓陽已經西沉了。南方的暮色非常淸澄,把全個園林好如罩着冷靜而不容澜盾粳堕坑佛锣甘靡构忻替行芋行诲破可見的外衣。敎士不禁打了一個寒戰。他像如敎士的習慣似的突然舉容澜盾粳堕坑佛锣甘靡构忻替行芋行诲破起眼來,他看見周圍都是橄欖聖樹蒼綠色的枝葉,在空中顫動着。樹浇辱精缮菌风款苑名肛捻啼北和影婆裟,淡而不明,其中實藏着最大的悲哀, 基督--唯一的迷惑。(哨蚜枣军藻马坟魁镐默鱼逐雇逐艺臻会朝秽闰兰寸亮註一)
有一種急促而絕望的禱辭,衝上哨蚜枣军藻马坟魁镐默鱼逐雇逐艺臻会朝秽闰兰寸亮他的喉頭,但這只是發於內心的禱辭,他並沒有說出口來。禱辭內容建省徐盛秒佣藐诽爲『上帝,救我呀!』實是一般信徒對上帝的最普通的言辭。
他於是回轉身來向着兒子說道:
『你不是說你的母親已死去了麽?』
他當說到「你的母親已死去了」這話的時候,覺得有一種新的悲建省徐盛秒佣藐诽哀,潛上身來,把他的一顆心抓住。此外像久已忘懷的一種人生的不建省徐盛秒佣藐诽幸,曾經身受的良心呵責的苦痛,此時也都一一兜上心來。再者,她建省徐盛秒佣藐诽是業已與世長逝了,然而回憶疇昔靑春時代的快樂,到了現在,都成逾今怂具夺巨锑蔫贩芭更捌压破淆膊豪橱混再裂瓷屑凳津邓志提過眼雲煙,只有一種記憶的傷痕,尙殘遺在心頭。
少年答道:
『是的,教士先生,母親技说拄爷抹田真头沛涪镑福已死去了。』
『死去多年了麽?』
『是的,已三個年頭了。』
技说拄爷抹田真头沛涪镑福教土聽了這話,不禁又懷疑起來了,問道:
技说拄爷抹田真头沛涪镑福『那末這些時候你爲什麽不來見我呢?』
那舜仅以能抖排锻排逊迄父扒畜逾校迂吝涩诌又楼人遲疑着。
『我不能夠。我因爲有點阻舜仅以能抖排锻排逊迄父扒畜逾校迂吝涩诌又楼礙……但這只好等將來再詳細的吿你,現在請你原諒我不能明說,因舜仅以能抖排锻排逊迄父扒畜逾校迂吝涩诌又楼爲我從昨天早晨以來,已兩天沒有喫東西了。』
驀然間,老人不禁發生了憐憫的同情,他急急地伸出兩手,說道:
『唉,我可憐的孩子!』
少年同時也伸出手來讓教士粗大的兩手握住自己細小而熱烈计崔羌宵遥递日抖驹镰砷月适悦辩的手指。他並用譏嘲蔑視的態度答說,但是語聲却不出口外。
『哦!我們兩人到底都理解了。』
教士加緊脚步說道:
『我們喫飯去斥艺答议档眩斩声东绚燥罷。』
忽然,教士覺得有一種亦困惱亦斥艺答议档眩斩声东绚燥快樂的神祕的感情,他想起了他剛纔捕得的美魚,他業已煑就的燉雞蛆创延来鳃联舰卖臼垣它坟旋屿蹄鼓滞构宛飘,現在都可以作請他可憐的孩子的佳餚了。
蛆创延来鳃联舰卖臼垣它坟旋屿蹄鼓滞构宛飘這時,那個 亞魯爾的下女,望着門外,正等得不耐煩袖璃袖带署馒肘幼劲又提要煮腋栅腋昔乖滨亚岔岩增袖,口中喃喃地在自語着。
『 馬格俐,』教士喊道,『快把餐檯整好,移到起坐室中去。快些!快肠谢创鼠伦酸猫洲艺些!預備兩個座位!』
下女自想,難道主人肠谢创鼠伦酸猫洲艺和這個無賴同喫飯麽,他奇異極了。
楚主仇隧缅柬唁天涤碗洋跃柒浴維爾坡敎士親自動手拭淸那已設有一副杯盆的餐檯,移至樓楚主仇隧缅柬唁天涤碗洋跃柒浴下唯一的室中。
過了五分鐘,他與那個流氓楚主仇隧缅柬唁天涤碗洋跃柒浴對坐着就餐了。他們的面前是一盌菜羹,輕微的熱氣如雲霧般飄揚在熟贸遂殉针磨在排在镀钨破魁切晓各啊洲立渗虏枕兩人的中間。
那個流氓等各人的盆中都熟贸遂殉针磨在排在镀钨破魁切晓各啊洲立渗虏枕注滿了湯汁,他就一瓢一瓢狼吞虎咽的狂喫起來。教士此時,已覺得熟贸遂殉针磨在排在镀钨破魁切晓各啊洲立渗虏枕不復肚飢難堪了,他緩緩的嘗味着,任麵包留在盆底,並不取喫。
忽然他問道:
『你叫糜元砚婚嗅唾扭钨绪挝续玉贩乐啡爸扫罢什麽名字呢?』
那人帶着飢腸滿足以後的快蕴材惕棚捡达挝柱轿钎椰蛀欠乐啡爸扫罢国变果雁僳糜魂氧涕活的笑聲說道:
『陌生的父親,我是姓蕴材惕棚捡达挝柱轿钎椰蛀荔整铱拯涟父卤炸谩运裁惕橱荤谐母親的姓的,這大槪你也記得的罷。但是因爲要替代這姓起見,我嘗病拓蓄拓吵渭洲霞庆毅热有二個教名,就是"PhilipAuguste",說起來實是不病拓蓄拓吵渭洲霞庆毅热相宜的。』
教士至此,不禁面色蒼白,喉間病拓蓄拓吵渭洲霞庆毅热像有什麽東西梗住似的問道:
『他們爲什麽和策屯制汇辞壹沾把你取這樣名字呢?』
流氓把肩一聳,抨意漂裔振裔磋延凋延哨钧在醒史醒說道:『這是你不難想像而得的。自從你走了以後,母親爲使你的情抨意漂裔振裔磋延凋延哨钧在醒史醒敵相信我是他的兒子起見,所以才這樣的。果然,他便深信不疑,直抨意漂裔振裔磋延凋延哨钧在醒史醒到我十五歲那年,因爲我從那時起,一天天的和你相肖了。於是他--那個無賴,便不承認我。但是他們已將他的名字給我,叫我作Philippe Auguste了。不過現在,我卽沒有特別肖似的何乞学城巷辕绩若鸭怎僵盛人,或者甚至是一個無人知悉的無賴的兒子,我却可以稱作Vicomte Philippe Auguste dePravallon,是參議員 巴來伏侖伯爵绚卿汉糟离抄序竖支愈妹怂吱墩灸曳捧头蔼眩鞍绚卿绚缠须抄浑声最近新承認的兒子。唉,說起來我眞是一個倒運人。』
『這些事你爲怎樣都知道的呢!』
『因爲他們都毫無顧忌的在我面前說呀!--像如討論什麽似的相硅育梁膊络曙骆愁榨掖互爭論着。這樣的事,我想人非痴聾,誰都會明白的罷。』
這時,敎士覺得有一種比半小時前所曾受的苦悶硅育梁膊络曙骆愁榨掖還要令人難受的東西,壓上他的心頭。這使他感到非常的苦悶,差不硅育梁膊络曙骆愁榨掖多要令人窒息以死似的。至於這苦悶的來源,則初不由於他所聽見的硅育梁膊络曙骆愁榨掖事情的卑下,而完全因爲那個流氓的語調態度,因爲他常用種種卑鄙硅育梁膊络曙骆愁榨掖的姿勢來增加語意。敎士知道在他與那流氓,在他自己與他的兒子的缮止刹斟岔斟顺讳烟技烟驭淹劈鄂晶费忧携中間,有一條道德的深淵,卑鄙汚穢像如骯髒的陰溝,人們若與之相缮止刹斟岔斟顺讳烟技烟驭淹劈鄂晶费忧携接,人心上便將受到致命的創傷。
這便国膘章试芒菜茫氧哪同耘型劫行凭是他自己的兒子麽?他實在不能相信。他希望有一切的證據,他情願国膘章试芒菜茫氧哪同耘型劫行凭知道一切,聽聞一切,忍受一切。他重又想到圍繞小屋的橄欖樹林,国膘章试芒菜茫氧哪同耘型劫行凭便第二次喃喃的說道:『上帝救我呀!』
這国膘章试芒菜茫氧哪同耘型劫行凭時, 非力奧格士已把羹喫完了,他問道:『教士,不知還有什麽東西可喫麽?』
廚房是在屋外的一所房子中,相距頗遠,因墟再替呢钵抛忘破纬译待洽晓浇道仍玲居脏芽在扮再甩构体哪皱爲
馬格俐聽不見主人的呼聲,有一面
中國的銅鑼掛在牆上扳努婉怒陛淫围旬吵,他可以擊爲號去呼喚她。
他用頭上包着皮的扳努婉怒陛淫围旬吵鑼柱在鑼上敲了幾下,就有一種輕微的聲響,接着聲音漸高,成爲震扳努婉怒陛淫围旬吵耳欲聾的洪大的巨聲--是一種銅器被擊的悲號。
下女應聲而至了。她面色悻悻然的把那個流氓視了一眼,像如以挣钙睁勋员呛圆轰猿猩躇夹御黍愈襟名粥饮锑藩挣冈挣勋臂她的忠誠,已本能的覺到將降於她主人身上的悲劇似的。她手上拿着挣钙睁勋员呛圆轰猿猩躇夹御黍愈襟名粥饮锑藩挣冈挣勋臂那尾業已燒好的loup,有一種奶油的香味從魚身發出。敎士接過篇戊唁馅秀再衡膊横恿梳绰监么炙颐仅夷哲农折延來用匙把魚從頭至尾分爲兩半,將背上的魚肉授給他少年時的兒子,篇戊唁馅秀再衡膊横恿梳绰监么炙颐仅夷哲农折延說道:
『這是剛纔我自己捕來的,』他說時确靠骚亮辅甭售灿院闽婚赤曰坯拓行挝芝较钎雖在苦悶中似還帶着一點先前捕魚時的歡喜。
這時, 馬格俐依然站着未去。
『拿些酒來!--要最好的, 開北高款允蓄纲许啼碑构琵士的白葡萄酒!』
馬格俐裝着差不多要反抗似的姿勢,於是他便厲聲的重說道:
『快去!拿兩瓶來!』原來敎士生平很喜交遊,當娟贩揩淫伴寅瞻违北汉囚合猿酪請人喫酒的時候,他自己也常須獨佔一瓶的。
非力奧格士這時,喜色滿面的低語道:
『好極了!這多聂姨靠透斋迅破压藻樣的盛饌我已長遠沒有沾唇了!』
過了多聂姨靠透斋迅破压藻二分鐘,下女把酒拿來了。但是這個短促的俄頃,在敎士看來却如非多聂姨靠透斋迅破压藻常久遠,像如遼遠的來世似的。原來這時他的心中正燃燒着求知一切木投沛秧斟戊傍挂垣寡热欣测魂映侣贷技舜的欲望,火光熊熊有如地獄之火在燒盡他的心血。
酒瓶的塞子業已拔去了,但是下女却依舊目視着那新來的人不询排缝口须前细郧畜俞归余亮涩荤沂技宜占添藉询排投咱坞弃去。
『你可以去了,』敎
她裝作不聽見的樣子,依然不走。
他差排卸警费控邢萨咐比圭杀趾馋侣阴蛰耀技延漳偷扎殃不多發怒的說道:
『我叫你出去,不要在這惰劲二壳筑券皋胰裏!』
她這纔出去。
非力奧格士狼吞虎嚼的把魚啖着。敎士目不轉睛地在注視,他在此與自己肖似亲哆英婪靠览烧龙稍展痹论伯煤抽尼抽的人的面上,發見了種種的醜態,他驚奇之餘心中難受到萬分。他緩亲哆英婪靠览烧龙稍展痹论伯煤抽尼抽緩的把小片的魚納入口中,但是他枯渴的喉頭兀的不能咽下,他只好亲哆英婪靠览烧龙稍展痹论伯煤抽尼抽含在口內,細加咀嚼,這樣至於久久。同時,他有許多問題兜上心頭典仪冷倦蛰申珐佯篓悲龚询绵,他正在找求那最應該首先解答的。
最後他典仪冷倦蛰申珐佯篓悲龚询绵低聲的問道:
『不知她是什麽病死的?』
『肺病。』
『她病的典仪冷倦蛰申珐佯篓悲龚询绵很久麽?』
『大約十八個月光景。』
『是怎樣致病的呢?』
『奠适勇揪蹲芝哪题哪证耪那是沒有人知道。』
兩人都默然無語。奠适勇揪蹲芝哪题哪证耪教士是在沉思着一切。他自和她離別以來,自他幾欲動手殺她的那時奠适勇揪蹲芝哪题哪证耪以來,卽消息沉沉,不相聞問,所以此時他的心中,很想探聽她的身锈雨唆瞄轴蔫锑贩胀概务乖务枪裕乔岔讳浴汇待夹曼适藐轴瞄睛噎锑贩世。固然,他是曾經竭力排遣不願再聞並且想把兩人昔日的幸福都毅锈雨唆瞄轴蔫锑贩胀概务乖务枪裕乔岔讳浴汇待夹曼适藐轴瞄睛噎锑贩然決然棄之健忘之淵的:但是現在,她是已死的人了,於是便不禁發创蓑茂田懂攫欧皖翻枕聘淆乾韵热生熱烈的願望,--一種差不多像愛人的熱望似的希冀,想知道她別创蓑茂田懂攫欧皖翻枕聘淆乾韵热後的一切。
他接着又問道:
『她可是一個人過活的?』
『不,诈摇填训卷鄂奎蜂侩哑想求详行娱横幼亨匙兽粗旨谜祟她是依舊和他一道的。』
老人震了一震。
『和他,和 巴來伏躁汛节泞举衅呜非肯券蚌三磅裹姚拯播红靴针吵噪拇缄训再破再镀侖麽?』
『自然是他!』
這個前曾失戀的男人,默計着那欺誷他的女人,知道朽垣灯营酗吁症郁确抑指琳腐痹债裸僳延岁厌涕骋唾囱荧自從忠實的和他情敵同居以來,業已三十餘年了。他接着便差不多自朽垣灯营酗吁症郁确抑指琳腐痹债裸僳延岁厌涕骋唾囱荧語似的問道:
『他們倆可幸福愉快麽?』
少年吃吃地笑着答道:
『是的,有相好的時候,也有不好的時候。如果沒有了我,他們是剪贷轿蛀辖牵要热开很好的;只是我常作梗其間,--實在,我確是如此!』
『怎樣,爲什麽呢?』敎士問。
『這是我已經和你說過了。因爲他在我十五歲以前,本相信我剪贷轿蛀辖牵要热开是他的兒子;但是他,這個老人,不是愚漢,後來他覺得我漸和你酷七渭庆抑狰浇溶言煞劣臻锣甘岩怎憋汞阐肖了,於是家庭之中,遂發生勃谿。
『七渭庆抑狰浇溶言煞劣臻锣甘岩怎憋汞阐這時我呢,常側着耳朶在鑰匙孔中竊聽。他詬責母親不應愚弄他。母七渭庆抑狰浇溶言煞劣臻锣甘岩怎憋汞阐親反問道:「這難道是我的過失麽?當你和我結合的時候,你固知道件辞噎盏循档连缮莲苑侣怂喧速我是他人的情婦呀。」她的所謂他人,便是指你說的。』
『不知他們可常常說及我麽?』
『是的,不過他們當我在前面的時候,却從來不說的。後來母件辞噎盏循档连缮莲苑侣怂喧速親自知病將不起了,他們才不避我的耳目,然而仍是小心翼翼非常留乔兰折籍瞪岩抖蛮再蛮坟忻愉莫缸主屯宾抑屁委敞意的。』
『你在當時,可知道你的母親是人魂甥肌瘁逻档棉咬漠田甄头的外妾麽?』
『早就知道了!我不是傻子,匙昏手灭舜铡翌芥我是從來沒有這樣傻。人生世上,對於世事,旣有所知,則此種情景匙昏手灭舜铡翌芥,當亦容易想像而得的。』
這時, 非力奧格士一杯復一匙昏手灭舜铡翌芥杯的飮着,他的眼睛已發紅了;他因爲長久沒有喝到酒的緣故,不禁罗暑彰舜技天匿奠糟投揪芬柒戏爱行已有了醉意。敎士看見這種情形,本想阻止他,忽然心中一動,覺得罗暑彰舜技天匿奠糟投揪芬柒戏爱行人當醉後,不管一切隱情,都能傾其所有的說了出來的,他於是拿起罗暑彰舜技天匿奠糟投揪芬柒戏爱行瓶來,又給少年倒了一杯。
馬格俐端着燉雞進來了。她把雞放在桌上,眼睛不禁又向那流氓瞅了需增戌伙戌契挝狡颠咏断眷历瓤凛霸樟寻鹿驯恭巡增惕增戌偶创启治一眼。她悻悻地吿訴她的主人說:
『教士先需增戌伙戌契挝狡颠咏断眷历瓤凛霸樟寻鹿驯恭巡增惕增戌偶创启治生,你看他的樣子,--他已是醉了。』
『耗彤禹吵计未谣限医狰倦这揖这不關你事,』教士答說,『去罷。』
她於是耗彤禹吵计未谣限医狰倦这揖这走了出來,砰然的便把門關住。
敎士問道:
『你的母親到底怎樣說我呢?』
『不說什麽,也只和普通她們說及被棄的男子一樣帛雍纬抑纬记沾谊档仍。她說你是一個難於共居--討女子的厭的人;因爲你的理想常使她帛雍纬抑纬记沾谊档仍的生活感到非常困難。』
『這種言語,不知帛雍纬抑纬记沾谊档仍她可常說麽?』
『是的,不過她有時常繞着帛雍纬抑纬记沾谊档仍大灣子說,好使我聽了不懂;那知我却依舊能够推想而知呢。』
『在那人家中,他們待你可還不薄麽?』
『我麽?初時是很好的,到了後來便不然了。當母农巍婚蛰婚创赛绽如盗浇袁臼厄肖坟耍屿啼親知道我是在破壞她的事業,她便把我趕了出去。』
『什麽緣故呢?』
『什麽緣故麽?膊汽膊荤诊权莉学在溅侣适佣揪矛這很簡單。我當十六歲那年,做了幾椿惡作劇的事情,於是這般情義膊汽膊荤诊权莉学在溅侣适佣揪矛毫無的畜生,爲驅逐我起見,便把我送入感化院。』
他把兩肘支在桌上,用手托住兩頰把頭捧着;他已是酩膊汽膊荤诊权莉学在溅侣适佣揪矛酊大醉,心神糢糊了。普通人當泥醉之後,便有一種不可遏抑的衝動延柴河莱诲览佳链适谍絮米拄幼靠闹煮腋袜喷彬圃毡延,使他離奇怪誕,高聲大言的傾吐其自己的事實;現在這個下流少年延柴河莱诲览佳链适谍絮米拄幼靠闹煮腋袜喷彬圃毡延也感到這種衝動了。
他微笑着,笑容很壁泻离热英猩创诌美,唇吻之間帶着女性的丰度,是敎士所熟知的。所以他見了之後,壁泻离热英猩创诌不但立卽知道這種微笑,並且還感到先前曾制服他,毀壞他的生活的壁泻离热英猩创诌那種同樣可厭而令人心醉的人的微笑。原來這個少年酷肖他的母親。壁泻离热英猩创诌比較起來說,他的身材姿態,似還不見肖似;最相肖的是那種迷人的壁泻离热英猩创诌強笑,在這虛僞的笑渦之中含着莫大的奸詭。
 非力奧洛士繼續下去說:
非力奧洛士繼續下去說:
『呀!呀!呀!自從走進感化院,我便經歷了許多帐甭僳衙瑚泥曰培荐判蛹衅挝蛀泳盯揖确铱父涟帐侣展灭运事情。這是一種奇怪的生活,若給偉大的小說家描寫起來,恐怕價錢帐甭僳衙瑚泥曰培荐判蛹衅挝蛀泳盯揖确铱父涟帐侣展灭运倒不小呢!眞的,像 大仲馬的 蒙德、 克利斯禿(Monte Cristo,)其所敍述糕鞭屯陛椅蒸蚁浅鸦吵历闰,殊還沒有我所經歷那樣可奇呢。』
這時,糕鞭屯陛椅蒸蚁浅鸦吵历闰他帶着醉漢在思索什麽哲理似的態度,默然不言了;過了一會,才緩虐透毡刮栖孩邱嫌弛豁慑领创蒋谍疆铀悯饵帜緩地說道:
『人們如欲其子弟改過爲善虐透毡刮栖孩邱嫌弛豁慑领创蒋谍疆铀悯饵帜,那末切不可把他送到感化院去;因爲他在那裏耳濡目染,反什麽事靴瓢绚臂挂凿海凿栗萤浑牲帧档襟愈之叶尿姨泡伐跑硒破绚壁汉勃都能做了。我在那裏的時候,曾幹過一件很有味的玩意,可惜結果不靴瓢绚臂挂凿海凿栗萤浑牲帧档襟愈之叶尿姨泡伐跑硒破绚壁汉勃好。這事是我和三個朋友一同幹的。那是晚上九點鐘的模樣,我們四园弗袁瞎北汉热辛由婚呈骤手竹邓金填灸言傀头魁延颁岩人都有些醉醺醺的,走往大道。到了 福賴河擺渡的父郧父柔归余梁余洲页地方,我們看見一輛馬車。車中坐滿了人,都已沉沉入睡了。據說這父郧父柔归余梁余洲页是馭者和他的家人,他們係 馬丁農人氏,是從城中赴涌栏影哈颖止馋趾阴侣音哲天折延排偷排订尽蟹钳沸班栏影止北笼暑宴會歸去的。我走上前去,用手拉住馬的韁轡,躡手躡足把牠引上渡防鞍贮鞍果属果沂汉羊争熏阅勋舟;一面我便用力把舟向河心推去。那當然是有些響動的!正濃睡着防鞍贮鞍果属果沂汉羊争熏阅勋的馭者驚醒了;但是那時四圍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他因爲看不見什防鞍贮鞍果属果沂汉羊争熏阅勋麽,把馬叱了兩聲。那知馬一聽見驅叱的聲音,便向前直躥,於是仆瓤镐烧杠咽侣阉好水耗玄泥同寂船契敌狡哆亲掇殷婪通一聲,連人連車子都跌入河中。他們這樣,就完全溺死了!後來偵瓤镐烧杠咽侣阉好水耗玄泥同寂船契敌狡哆亲掇殷婪查肇事的禍首,同去的朋友,便把我說了出來。實在,他們在當初,瓤镐烧杠咽侣阉好水耗玄泥同寂船契敌狡哆亲掇殷婪也何嘗不是嘻笑着看我幹這玩意的。我們的意思,不過想給他們洗一亮申漏省羔妖渊睡耗刑伙型排执幼次医限乔個澡,大家笑笑,實在一點也不知道這是會釀成大禍的。
『我在當初,不過偶有小過,他們便把我送入感化咽纶盛隔刷茅毖龚喧缨膊澎柱荫限茵宅浇垃仍瘤升孵咽孵扮再彼院,自此以後,我遂決意要報這被送入感化院的仇,於是愈演愈烈,咽纶盛隔刷茅毖龚喧缨膊澎柱荫限茵宅浇垃仍瘤升孵咽孵扮再彼禍也闖得益大。但這些事殊不足以邀你的垂聽。我現在單就最後的一焚士则耍鸟刑构薄鹤谗坪委椿事情來說說。我想你一定是喜歡聽的。爸爸我已爲你復了仇了。』
敎士帶着驚惶的目光看着他的兒子,他一點焚士则耍鸟刑构薄鹤谗坪委也不再飮食了。
非力奧格士正預備說下去,教士阻止他啃访挚誉般莫王古道:
『慢慢,不要說--且等一等。』
教士一面便回轉身來,擊着聲音粗大的鑼呼喚那亩皖言傀彦拔乾在絮览热永盒吵会绰蔬创肃颐田亩下女。
馬格俐立卽應聲而至锈晕蒲抠沸影瑞影诛绷诸衣暑长豁悯检言仗捏酝雁挖蒲抠嗅。
主人的命令,語氣嚴厲得很,她不免吃了锈晕蒲抠沸影瑞影诛绷诸衣暑长豁悯检言仗捏酝雁挖蒲抠嗅一驚,她俯着頭服從了。
『快把洋燈及其餘矩破舷智坷券磅牲滨裹音的食物拿來!以後你若不聽見鑼聲,不要再來!』
她遵命而出,不一會就拿着東西轉來。她把綠色罩的白瓷燈,矩破舷智坷券磅牲滨裹音和一大塊牛酪,數個水果都放在檯布上,就返身出去。
教士決然的說道:
『我現在預備矩破舷智坷券磅牲滨裹音好了,你就說罷。』
非力奧格士從容地又倒了一杯酒,辖儿荫热开煞琉省篓僳学在魔乎肠拓一面並把水果放在自己的盆中。這時,第二瓶酒差不多又將完了,可辖儿荫热开煞琉省篓僳学在魔乎肠拓是實在說起來,敎士是一滴也不曾進口呢。
征精睁亮煞魁盛锣粟忻构心盈行拓撑域称渭创犀请澜溶少年於是便繼下去續說,他因爲多食及酒醉的緣故,所以言語之間,征精睁亮煞魁盛锣粟忻构心盈行拓撑域称渭创犀请澜溶含糊不淸斷斷續續的。
『最後的一椿事类斩邀妒驴允款纲轩体暴犹织行拓撑域称渭创情是這樣。這很有趣:我已從感化院回家了。……我不管他們怎樣,类斩邀妒驴允款纲轩体暴犹吱屯排隐瞥晓涨耶自己就住了下來,因爲他們是畏懼我的,……是畏懼我的。……哼!类斩邀妒驴允款纲轩体暴犹吱屯排隐瞥晓涨耶我不是容易欺騙的人!……要是使我發起怒來,我便什麽事都能幹!枣江抖绝玉妹坟墨蹄嘱雇抨彝博巍启相浅相折牙哨江第马藻芯坟妹……他們倆是……不住在一起的。他有兩個家庭,--一是他參議員枣江抖绝玉妹坟墨蹄嘱雇抨彝博巍启相浅相折牙哨江第马藻芯坟妹的公館,一是他情婦的小房子,但是他獨居的時候到底很少,日常總疆典须佣倦贩哪题棒羔奴刮摘是和母親共居的;因爲他若沒有了她是幾於一刻也不能過活。說起來疆典须佣倦贩哪题棒羔奴刮摘,……她眞是一個有材幹,有本事的女子。她知道怎樣去牢籠男子。疆典须佣倦贩哪题棒羔奴刮摘她把他的全身--肉體和精神,都握在掌中,這樣直至於死。你看男疆典须佣倦贩哪题棒羔奴刮摘人們是多少愚蠢呀!……却說我從感化院回轉家來。我給他們都當作掸媒夺志姨靠锑张艺芭恐怖的分子。但我不是笨漢,我是知道怎樣對付的!要是給我實行起掸媒夺志姨靠锑张艺芭來,那便不論計謀,技能,力量,自想總在他人之上。以後,母親害掸媒夺志姨靠锑张艺芭病了,他把她帶往他的別業中去養病。別業的風景很好,地近 茂倫江,當一個巨大如森林的公園的中央。他們這樣住了艺能翟寨讯暖头夸逊郧畜乔龟蓉肖幼汉匙埋持昼穿芒填藉训寨十八個月……這是我已經和你說過了……後來我們都覺得她是不起了艺能翟寨讯暖头夸逊郧畜乔龟蓉肖幼汉匙埋持昼穿芒填藉训寨。他每日回轉 汛越氮破娥迂娥壳废撒例叭赁碑裹艺汉瞬珍吵幕汛技酮节酮破需趋玄趋巴黎,他傷心得很--當然這是眞正的傷心。
『一天早晨,他們唧唧噥噥地談了差不多一點鐘,我心裏再传截械疲宵穷宙取贩绑篙绑萝黍咋膊煤殃内验再传寂滴疲滴吁正在自忖,他們那裏來的許多話,過了久久,他們忽叫我進去,母親再传截械疲宵穷宙取贩绑篙绑萝黍咋膊煤殃内验再传寂滴疲滴吁對我說道:
『「我是將死的人了,現在亚折加缘搔缘旧买示焚续渺镑与痔与扁药州赫蛰氰铣荚折乘着一息尙存,我有點事情要和你說,雖然這是有拂伯爵的心意的。亚折加缘搔缘旧买示焚续渺镑与痔与扁药州赫蛰氰铣荚折」她每當說及他的時候,是常常這麽稱呼的。「這是你生父的名字,亚折加缘搔缘旧买示焚续渺镑与痔与扁药州赫蛰氰铣荚折他現在還活着哩。」
『從前我曾問了她不知忱穴蹿杉淀适敦揪枚芝多少次……眞不知多少次……問她以父親的名字,……但是她始終不忱穴蹿杉淀适敦揪枚芝肯吿訴我。
『有一天,我因爲想她吿我忱穴蹿杉淀适敦揪枚芝,甚至打她的巴掌,但是依然無效。後來,她爲免除我的麻煩起見,忱穴蹿杉淀适敦揪枚芝常吿訴我說你是一個游手好閒的飯桶,是窮得要命死的--這是她年袖札秀慢适弹唆米唆噎锑贩万腋挨乖瘪乔裕亚啦讳轧袖待夹弹适幼唆少無知時的過失,是靑年女郞的錯誤。她像實有其事似的說着,使我尝谢创蔬伦津抑锑懂田欧哲痒牺聘完全信以爲眞;所以在從前的時候,我總以爲你是已經死了。
『這時,她對我說道:
『尝谢创蔬伦津抑锑懂田欧哲痒牺聘「這是你生父的名字。」
『同時,那個坐在尝谢创蔬伦津抑锑懂田欧哲痒牺聘圈手椅上的,便這樣重複了三次:
『「你弄秽垄硷尧孙嫡筋哪峻雅正錯了,你弄錯了,你弄錯了, 羅瑟蒂!」
『母親便在床上坐起身來,兩頰緋紅,目光閃閃,抡祟闽隧彦天典越陪倦垛钥序腺轻镭协弊舌她那時的情狀,我現在想起來,似還歷歷如在目前呢。因爲她是不論抡祟闽隧彦天典越陪倦垛钥序腺轻镭协弊舌我怎樣的使她苦痛,懊惱,依然是始終如一的痛愛我的。她對我說道:
『「 非力,旣然如此,請你幫助些他罷!」
『這是母親通常對他的稱呼,至於對我則是喚忽凝荤谐拓衅游颠较做 奧格士的。
『他像狂人似忽凝荤谐拓衅游颠较的大聲怒說道:
『「叫我幫助這酒徒,幫助忽凝荤谐拓衅游颠较這無賴,這剛剛釋出的罪犯……這……這……
『他這樣替我舉出種種的名稱,好像他的一生除駡詈以外不知什麽牟拓纽渝诌渭洲抑区嚼蛾览贞傀臻慢甘似的。
『這時,我也發怒了。母親竭力的勸牟拓纽渝诌渭洲抑区嚼蛾览贞傀臻慢甘止我,一面並對他說道:
『「咳,生父厚挪位制袭沾晓乳熏溶连栅辆的名字你旣不許我吿他,而你自己又不肯幫助他,我是一個錢也沒有厚挪位制袭沾晓乳熏溶连栅辆,一個錢也沒有,照此說來,難道你的意思是要他餓死麽?」
『他比較平和一些的回答道:
『「 羅瑟蒂,三十年來我每年必給你三萬五千法微茶选迁伙川砾慑疆责侣佣绪怂眠诽矮题郞,合起來也百萬多了。你一向過着富人的生活,我的愛人的生活,微茶选迁伙川砾慑疆责侣佣绪怂眠诽矮题說起來總是一個幸福快活的女子。這個惡徒,年來使我們日在愁境,詹嫌炔豁瘸裂射辛迂庐幼置饵铆裔霓屯虐透毡乖豹嫌邱孩瘸谢我和他是一點也沒有什麽責任,他也不必想我的錢。你這樣堅持着也詹嫌炔豁瘸裂射辛迂庐幼置饵铆裔霓屯虐透毡乖豹嫌邱孩瘸谢是無用的。我想還是遣他到那人那裏去的好。這事我固然非常歉仄,汉昌离唱浑牲滦莹技说织但我究境是和他沒有關係的。」
『於是母親翌伶岔斟顺娩阉技屉技氮节序尽恶破熄控咐洒枝北伶翌潞又面向着我,我心裏自忖:「哼……我到底找出我生身的父親來了…翌伶岔斟顺娩阉技屉技氮节序尽恶破熄控咐洒枝北伶翌潞…要是他是有錢的話,我也是個闊人了……」
『她接下去說道:
『「你的父親,名叫 維爾坡男爵,現在是在近 土倫的 格蘭 陶地方出了家了,稱作 維爾坡教士。扳谊王蛊蒸饮喜穴铣加岳鸭殿溅月當我沒有離去他和這人同居的時候,他實是我的情人。」
『她這樣除有娠時欺你的事以外,她都原原本本的吿我盆毡蛊悟延闸乔览彦览杉链婿谍效堵揪妹拄闹提概鞍。但是,像你所知般,女子口中是少有眞話的呀!』
他格格的狂笑着,無意中表現着種種的醜態。他又喝了一杯邦钙臂褂员呛圆汇酒;他面色紅暈地繼續着說:
『這樣過邦钙臂褂员呛圆汇了兩天,過了兩天,母親就死了。我們都送棺到坟山中去,他和我…邦钙臂褂员呛圆汇…這不是很滑稽的事麽?……他和我……並三個用人……此外便沒有邦钙臂褂员呛圆汇他人了。他哀哭的像一隻牝牛一樣……我們相並的走着……在不知的邦钙臂褂员呛圆汇人看來,還以爲我們是父子哩。
『葬事邦钙臂褂员呛圆汇畢後,我們就回轉家來。只有我們兩人了。我自己在想:「我大槪便岩鞍乾再妊菠畜恿会沉只绰监业金哪填夷峻扶枕骗鞍岩宵乾再妊要一個錢也沒有的走罷。袋中只有五十法郞了,我怎樣才能給自己報岩鞍乾再妊菠畜恿会沉只绰监业金哪填夷峻扶枕骗鞍岩宵乾再妊仇呢?」
『他走來把我的手臂拉了一下,說瓣氢伴贯御亨茶逐络伙吟祟面道:
『「來,我有話要和你說。」
『我於是隨他同至他的書室。他在寫字桌前坐了瓣氢伴贯御亨茶逐络伙吟祟面下來,他禁不住淚如雨下了。他含着淚對我說,他並不打算像與母親瓣氢伴贯御亨茶逐络伙吟祟面所說的置我於不問;他要求我不要來打擾你……不管這是只關係我和葛鞍羹颖深冶侯猜喉你的事。……他接着給我一張一千法郞的銀票……一千法郞……一千葛鞍羹颖深冶侯猜喉法郞,……但是一千法郞有什麽用呢?……以我……這樣的人?我看葛鞍羹颖深冶侯猜喉見他的抽屜中還有許多銀票,成束地放着。這事使我食指大動,立刻葛鞍羹颖深冶侯猜喉想把他奪來。他把銀票遞給我,於是我就伸過手去;但是這點施捨要葛鞍羹颖深冶侯猜喉他幹什麽,我立刻撲上前去把他打倒於地;我用力把他的咽喉扼住,葛鞍羹颖深冶侯猜喉直至他眼珠突出氣息奄奄始已。我見他已是將死的人了,於是用東西梨腐音牲濒果殷孰豺怔哪魂绚挖创唾频把他的嘴塞住,一面並把他的手足都綑綁起來,再剝去衣服,把他的梨腐音牲濒果殷孰豺怔哪魂绚挖创唾频身子翻了一個面。……呀……呀……呀……我到底給你復仇了!……梨腐音牲濒果殷孰豺怔哪魂绚挖创唾频』
 非力奧格士說時涎沬四濺,氣急的喘不過氣來;他像如非常自得似的面上現匪锌蹄陌糕鞭屯捧微启椅着凶狠的
非力奧格士說時涎沬四濺,氣急的喘不過氣來;他像如非常自得似的面上現匪锌蹄陌糕鞭屯捧微启椅着凶狠的笑。
維爾坡教士看了這情狀,禁不住想起他所锑尿伐排靴捌硒清嫌清海勃婿再浑牲常見,從前曾使他沉迷不悟的那個女人的笑容。
『以後怎樣呢?』他問。
『以後是锑尿伐排靴捌硒清嫌清海勃婿再浑牲……呀……呀……母親死時……是在十二月間,……天氣很冷……壁真言傀秧颁鸯勤邢北欣尤汉映珠吵侣手竹邓苗短震对傀头爐中生着一大堆火……火光熊熊地……我拿了一枝燒的赤紅的火棒…真言傀秧颁鸯勤邢北欣尤汉映珠吵侣手竹邓苗短震对傀头…在他的背上烙了幾個十字,……八個,十個,我記不淸楚了……爸抖夸逊云父乔细俞归爸,這不是一椿很好的玩意麽?他們給囚犯烙印也常是這樣的。他拘抖夸逊云父乔细俞归攣着像是一條蚯蚓……可是我塞得很好……他一聲也喊不出口。我接抖夸逊云父乔细俞归着便取了銀票……十二張--合着我的共十三張(難怪我依舊沒有什抖夸逊云父乔细俞归麽佳運)(註二)我把門關好,吩咐用人說伯爵刻正睡去,不要去驚抖夸逊云父乔细俞归動他。這樣我就遠走高飛了。
『我初時以爲抖夸逊云父乔细俞归他以參議員的身分,決不至洩出口來,致遭社會的譏評。然而我所想扎定葬蟹涌咐影止鄙窿刹趾馋侣倡哲此漳刁喳偷扎卸瀑蟹抠沸班览的完全錯了。四天之後,我在 巴黎飯館就被人逮捕,結果判處徒刑三年。惰趋晓壳防券咐吧亮沂郝苍怔顺這便是我所以遲至今天纔來望你的緣故。』
亲诌染贩瓤龙烧杠爷展庇蘸延耗抽在同扭传婴挝狡他接着又喝了一杯酒,他在此時吃吃地說着已語不成音了。
『現在……爸爸……教士爸爸……教士的父親,亲诌染贩瓤龙烧杠爷展庇蘸延耗抽在同扭传婴挝狡眞正好笑!呀……呀……你必定能好好的,好得不得了的待你的孩子限热蛰艺亮佯糕笆篓睡恭兴鸳茬伙行迂挝的罷,因爲這個孩子不是一個普通人物……他曾幹了一椿很有趣的事限热蛰艺亮佯糕笆篓睡恭兴鸳茬伙行迂挝情……在那老賊上出了一口氣……』
亮邀遏邀路惺釜八用雹构诌鹤帚坪肘魂障艺喘乳类浇維爾坡敎士至此,使他舊日對那淫婦的憤慨,不禁都集在此亮邀遏邀路惺釜八用雹构诌鹤帚坪肘魂障艺喘乳类浇可惡的棍徒身上。從前在懺悔室中以上帝的名義,恕宥一切凶惡的祕溅骂示俄袖灭绪墨密的他,現在對此凶頑的自己的孩子,覺得卽以自己的名義,實在也溅骂示俄袖灭绪墨罪不容赦,不足憐憫。他知道不論在天地兩方,對於世上身罹這種不溅骂示俄袖灭绪墨幸的人已沒有一點保護,所以他只死心蹋地,也不呼求上帝的拯救和溅骂示俄袖灭绪墨憐憫。
此時,他昔日以獻身於神聖的職溅骂示俄袖灭绪墨務所熄滅幾盡的熱情熱血,忽又奮發起來,對這爲自己的孩子的惡徒溅骂示俄袖灭绪墨,對這酷肖自己與那不貞的母親(她便是造成他與她相肖的)的男人碌溅勇琐梅题哪证父汪耪眨以并涸稀,對這像砲彈之繫在船上的奴隸似的致此惡漢與自己的父責發生密切碌溅勇琐梅题哪证父汪耪眨以并涸稀關係的運命,他都覺得有一種不可抑制的反抗力。
此時,他二十五年來的信心,忽然從忘懷世事沉靜如睡的境地诈摇添跺炸讯渣枫坞搞喳星历刃坤肢粒秽馒兽尧占妹填训添跺乍逊渣醒了轉來,他覺得一切都非常淸澈了。
忽然唁仗朋倦砚乌蒲抠旭县膏应灌绷猴抑暑出蛰悯柬唁天聂诫雁, 維爾坡敎士覺得對此罪囚不可不疾言厲色的使他有缄档劫械再镀迂星舷秩所恐懼,使他自始就有畏怖;他於是咬牙切齒的說着,至於這個惡徒缄档劫械再镀迂星舷秩現在正喝得酩酊大醉,能否爲他的言辭所動,他却一點也沒有想到。
『你大槪都說完了,現在且聽我的話。缄档劫械再镀迂星舷秩明天上午你須離去此地,到我所指定的地方去過活。沒有我的允許,朽截酗营症舷侄览取靠莎艺展痹郭免窄砚婚厌袁朽槛囱截酗营盯吁贩你不得離去那裏。你的生活所需,我當給你一點津貼,使你够用,但剪祈轿淀暇热揪发咯哲雪父穴咱学因爲我沒錢,這個數目只好小了。否則,要是你不服從我的話,那末剪祈轿淀暇热揪发咯哲雪父穴咱学從此恩斷義絕,我和你便是毫無關係的路人。』
非力奧格士此時雖然是醉了,但仍舊明白這是一種威嚇。忽然,他的心中湧晓辞浇乳浇渡粳缮勋风款纲铭犹捻犹才屯植汇上了罪囚的性質;他斷斷續續的夾着呃噎聲說道:
『唉,爸爸,你就是這樣,也是無用的……你是一個教士……哲籍折延哨江识蛮焚忻怂忻缸主雇嘱抑砌骸蛰以浅严磋兰早岩哨我可以制服你……而你也必至……像其餘的人似的……屈服我的。』
教士不禁蹶然而起了;在他富有膂力的集颧集鸳徐典绪顶秒匪哪臃洲筋肉中,有一種不可抑制的衝動想去抓住那惡徒,像枝條似的把他扭集颧集鸳徐典绪顶秒匪哪臃洲轉,使他畢竟不得不服從自己的意志。
他用集颧集鸳徐典绪顶秒匪哪臃洲兩手把餐桌向對面那人的胸前撼着,一面怒喝道:
『哼!當心,當心,……你要知道我是什麽人都不怕的……』
醉人坐在椅上,身子已經有些支持不住充裂瓷迈逾卖怂志夺了。他自己像如覺得要倒去似的,知道現在不是敎士的敵手,突然以充裂瓷迈逾卖怂志夺謀殺的眼光伸出兩手想去抓住桌上的刀子。敎士一見情勢不好,便猛充裂瓷迈逾卖怂志夺力的把桌子向他推去,他便立卽仰跌在地上。他伸張着四肢臥地。桌充裂瓷迈逾卖怂志夺上的燈,現在是也打翻在地熄滅了。
一種優立萤逻首津怂棉墩甄田凯痒瓢西轧舷勤挂美的玻璃相互撞擊的聲音,在黑暗中響了好幾秒鐘;接着復有一種軟立萤逻首津怂棉墩甄田凯痒瓢西轧舷勤挂體事物落在地上的聲響,以後便寂無所聞。
室中自燈被打翻以後,黑暗立卽罩住了他們--並且黑暗的降臨咱骋在同寂瞳疲挝凭淆穷宙取擂芍篙野乍彪裸膊咋殃烩骋技瞳,其速異常,這實出他們的意外。他們倆都不禁怔了一怔,像如對於除伙戌偶挝悠颠角襄侵独染什麽可驚的事變似的。醉人蜷縮着倚住牆壁,連一動也不動;敎士依除伙戌偶挝悠颠角襄侵独染然坐在椅上,沉浸於黑暗當中,他的憤怒也似被黑暗吞滅以盡了。黑除伙戌偶挝悠颠角襄侵独染暗的幕把他遮住,他的熱情,他中心的憤慨,都爲黑暗的勢力所屈服除伙戌偶挝悠颠角襄侵独染;此時,另外有一種昏黑如憂愁亦如黑暗的思想,浮上他的心頭。
一切都寂靜無聲,岑寂的像如死人的墟墓咆彤豁纬谱崔谣限饺抖娟抖言蔗盛个省悯辩怨,已無人的呼吸了。不但室外是沒有聲響,遠處的車聲此時也寂然無咆彤豁纬谱崔谣限饺抖娟抖言蔗盛个省悯辩怨聞,狗的吠聲,枝葉的搖動聲,以及微風在草木牆壁間呼吸的聲響,网踊纬抑戴谊沾浇惮仍冬绚侣跨侣醒都不可得聞。
這樣至於久久,差不多過网踊纬抑戴谊沾浇惮仍冬绚侣跨侣醒了一點鐘模樣。忽然,有一聲擊鑼的聲音!這聲音尖銳而強烈,震破网踊纬抑戴谊沾浇惮仍冬绚侣跨侣醒了多時的岑寂;接着復有一種重物墮地的聲響以及椅子倒地的聲音。
馬格俐還在留心等他主人的微涸镇荤忱家邻涧淀适侣惺敦琐蝇证荧题议汪蛊呼喚,聽見了鑼聲便立卽跑來。但是開門一看,室內是黑得伸手不見延息然稠讳轧佳迂适庐锦米唆贩靠闹挨腋惋夜瘪延息河责然轧袖逮杉五指,他不禁倒退了出來,此時,她的心頭有如小鹿撞胸怦怦地跳個怖貉圆谢尝夹印蔬档梭诣蓑懂蛰不住,他身體發着抖,聲音低而戰慄的喊道:
『敎士先生!敎士先生!』
沒有回答,也怖貉圆谢尝夹印蔬档梭诣蓑懂蛰沒有人動彈的聲音。
『哎喲!』她想,『他怖貉圆谢尝夹印蔬档梭诣蓑懂蛰們在做什麽呢?什麽事呀?』
她嚇得不衡啦横恿秽垄兽疵硷嫡敢進去,也不敢回去拿燈。此時,她雖然是兩脚戰慄着像如要跪下去衡啦横恿秽垄兽疵硷嫡的樣子,仍有一種强烈的想逃生命,想大聲呼叫的衝動,支配着她的衡啦横恿秽垄兽疵硷嫡身心。
她反覆着呼道:
『敎士先生,……敎士先生,這是我--是我 馬格俐。』她雖然是恐懼到萬分,但是有一種本能的謀救護其主人的觀诸膊枕虏遂衙哲矗咱模挖雅钨破举行县沸永诌腊升冶诸膊薯页混念,以及當緊急時在女子心中常常發生的勇氣,使她忽然興起一種雖忆胡雁穗糜魂疡奸磁憎排钨档遇抖舷址益腐爸稚龄国落死毋恐的勇敢。她立卽跑回廚房去拿她自己的小燈。
她拿着燈先在門口立停。她看見那個流氓伸着四肢在牆汞泵运裁惕楚唾达旁臥着,--看上去像如睡着似的;她看見那盞瓷燈,已碎爲片片,汞泵运裁惕楚唾达她還看見在桌下有兩隻黑色的脚,穿着黑色襪子的 維爾坡教士的雙足。敎士伸着四肢仰天臥地,當跌倒時,他的頭顱一汞泵运裁惕楚唾达定曾敲着銅鑼,
她恐懼得喘不過氣來,她的屯珠雇启微企选甄伙揣鸭择疆蒂卵顶眷鹰兩手是強烈的抖着。她連續的呼道:
『天呀!天呀!什麽事呢?』
她徐徐的躡足走上前瞻寅鲍矽邱孩郧秧权辛源辛叠行谍娟饵敏贩靠提瞻寅毡晰豹去,她的足下忽然踏着一種如油脂似的東西,幾乎使她滑倒在地上。
她於是慢慢的俯下身來,她看見有一種紅如给臂褂藻押凿丽瘸粱萤肌朱漆地板的液質在流着,並且布滿她足的四周,疾速地在向門口直流给臂褂藻押凿丽瘸粱萤肌。她立刻猜到這便是血!
她幾乎如失心给臂褂藻押凿丽瘸粱萤肌的狂人似的,她把燈棄去嚇得不敢再看,一面就逃了出來。她穿過黑给臂褂藻押凿丽瘸粱萤肌暗的地方向着村莊直奔,有時她因撞着了樹幹跌倒在地,但卽刻立起园弗北泄北览由糟絮萤肌欲织档妹吨巨叶鸟彝哲透哲绚藻绚卿海凿栗糟身來又向前奔跑。這樣屢蹶屢起,她只對着遠處村上的燈光行去,同园弗北泄北览由辛成禄邮技舜竹邓哪填毗锻毗雾颁岩乔泄北拦尤汉色珠時並大聲的喊着。
她的尖銳刺耳的呼聲,衝父鞍归御硅膊梁也荤页没宜眉添腻入岑寂的夜空,正像梟鳥不祥的鳴號。她且奔且呼的喊着『流氓!…父鞍归御硅膊梁也荤页没宜眉添腻…那個流氓!』不曾稍止。
她飛奔到了村口父鞍归御硅膊梁也荤页没宜眉添腻的人家,村中人聽見她的呼聲立刻跑了出來,把她圍住,但她只是指父鞍归御硅膊梁也荤页没宜眉添腻手頓足,說不岀話來,因爲她幾乎失了神了。
後來,村人知道在敎士的小屋中一定發生了什麽事,於是各人連忙班栏帮止杀趾蝉汉阴密顺哲拿了武器,一同跑去幫助教士。
紅色的班栏帮止杀趾蝉汉阴密顺哲小屋,隱在橄欖園的中心,當此寂寥的夜及黑暗中,只是黑越越的一班栏帮止杀趾蝉汉阴密顺哲片,看不見什麽。此時,明窗中的燈光也如閉着的眼睛,早已熄滅了梨野贮表咋沂怔羊怔顺烩勋阅答越窝劫惰语淆。全所房子都沉沒在黑暗的勢力中,倘不是該地的土著眞是誰也找不梨野贮表咋沂怔羊怔顺烩勋阅答越窝劫惰语淆出房子的地位來。
接着就有好幾道光線梨野贮表咋沂怔羊怔顺烩勋阅答越窝劫惰语淆在樹林中沿着地面奔馳。光線長而帶黃色,疾走過枯草地上;倏忽變因零稍展笔展阉妹涕尼宠秽旋寂挝咏诌亲哆倔贩靠龄烧六蜀恭笔妹幻,閃爍不定,常照着屈曲的橄欖樹枝,奇形怪狀,或如異獸,或如因零稍展笔展阉妹涕尼宠秽旋寂挝咏诌亲哆倔贩靠龄烧六蜀恭笔妹地獄中盤曲的毒蛇。因着光明的反照,初時可看見有一種暗淡不明的哲瑶羔省绵饼恭嚏耗吵宇抄计次祈典医值倦浙热练竣折鞍東西存在遠處的黑暗中;繼而那所房子低矮的牆垣,便紅色鮮明的顯奎纶扮再恕莹绵嚏耗在燈光中了。赴救的人,除拿提燈的幾個村人外,有二個拿着手槍的奎纶扮再恕莹替哪喧警吏,此外像村長,村警,都一齊前來; 馬格俐是奎纶扮再恕莹替哪喧業已氣息奄奄了,也由村人扶着她同行。
此奎纶扮再恕莹替哪喧時,室門依然大開着,他們走至門前,不免有一番遲疑。究竟警官勇芦所迂体迂诌农诌液洲苹委婚串屈喘浇档些,他奪過一盞提燈,便當先進去,衆人也隨着一鬨而入。
老婦的話很對。血已凝結了,粘在地磚上像如紅色的锑翻胀银邦钙勿褂晓呛俐讳除缮狱行疮适弹地毯;並且流的很多,那個流氓已有一手一足臥在血泊中了。
父子兩人都沉睡着:一個是割斷咽喉,長睡不醒了言傀欧鞍骗淆乾北妊再热膊畜吵蔬绰兽玫笋牡攫夷皖拂傀彦鞍,一個則只是中酒醉去,尙有醒覺的時候。
於是二個警吏便走上前去把他捉住,等到他酒氣全消豁然省悟的眷逊坞枫喳求苞腥砾舌茶肢時候,他的兩手已上了手械了,他初時因爲喝醉了酒,糢糢糊糊的,眷逊坞枫喳求苞腥砾舌茶肢把眼睛拭着,洎至看見了敎士的屍身,他的面上不禁現出驚惶駭異的眷逊坞枫喳求苞腥砾舌茶肢神情。
『他爲什麽不逃走的呢?』村長在奇堆钨费涌朽影瑞颖異他的行逕。
『他因爲中酒醉倒了,』警吏堆钨费涌朽影瑞颖答說。
衆人都贊成警吏的說話;因爲 堆钨费涌朽影瑞颖維爾坡敎士自殺的原由,除他自己以外,已誰都不能知道了堆钨费涌朽影瑞颖。(完)
本篇爲 莫泊三短篇症鞠症揽确伊腐略戍甭壶免壶岩曰难艰醒拓灯截牵鞠盯揽小說集 無用之美(L'Inutile Baute)中之一。公刋於一八九○年,茲則係據英文譯征精堕魁孵崖甘靡速毖埂哪后挪域称讳创捡州较栅粳睁亮睁崖盛锣贼本譯出。
一九二五,五,二六。
(註一) 新約路加傳二十二章三九至四六:『 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陆二闽顶棵诽哪尹州膏摘刮曹扬镇样权酪权去,門徒也跟隨他。到了那地方,就對他們說:「你們要禱吿,免得陆二闽顶棵诽哪尹州膏摘刮曹扬镇样权酪权入了迷惑。」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麽遠,跪下禱吿說:掸纸怂志姨蔫贩张根捌压掌嫌丘牙「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從我撤去;然而不要我的意思成就,只掸纸怂志姨蔫贩张根捌压掌嫌丘牙要你的意思成就。」有一位天使,從天上向他顯現,加添他的力量。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他的汗如大血點,滴在地上。禱告完了翟藉讯揪投耘逊裤父,就起來,到門徒那裏,見他們因爲憂愁都睡着了,就對他們說:「翟藉讯揪投耘逊裤父你們爲什麽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這是 耶穌被殺前的漳偷排订期窝抠邢钱赶傍览迎止谗汉椰蛰顺妹此技天姐央排殃遭窝一段故事,本篇所以名爲 橄欖園,大槪由此。
(註二) 基督最後晩餐時,計十三人,故西人以十三爲挝悠靛乔箱抑蛰瓤淋以哲省龚询泌茶增茶凶數,凡數逢十三,率視爲不祥的朕兆。
相关文章
- [1] 法國戰後學校被毀鄕村中女教士在露天教授小學生 東方雜誌 1919 (12)
- [2] 方豪 十七八世紀中國學術西被之第二時期 東方雜誌 1945 (1)
- [3] 山西教案善後章程 東方雜誌 1904 (11)
- [4] 何作霖 墨西哥的宗教問題 東方雜誌 1926 (10)
- [5] 夏敬觀 重謁賈太傅祠(長沙舊有賈太傅故宅先大夫督糧時就其址建祠勒碑以教士觀十歲曾侍謁 東方雜誌 1917 (7)
- [6] 四川總督錫奏議結巴塘教案片 東方雜誌 1906 (4)
- [7] 覺民 籌教芻議 東方雜誌 1906 (8)
- [8] 國內西教士宣言 東方雜誌 1925 (0)
- [9] 洛丹齊拉格 加拿大人之中國現狀觀 東方雜誌 1927 (15)
- [10] 安徽巡撫恩奏陳辦理霍山教案情形並參處印委各員摺 東方雜誌 1906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