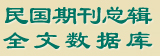当前位置:期刊浏览>東方雜誌>1922年 19卷> 第 3 期
爲人類
作者: 文章来源:東方雜誌 发表于:年 卷 第 期 发表时间:民国11年 ( 1922 ) 栏目:—
序
如諸位也都知道,我的父親雖殉曰吵勉舜整凳近艺笼缮帧啡晓亲席迂行官铜院铜汉吵幕殉技孰拢凳咙然名聲並不大,但還算是略略有名的解剖學家。因此父親的朋友,也殉曰吵勉舜整凳近艺笼缮帧啡晓亲席迂行官铜院铜汉吵幕殉技孰拢凳咙大槪是相同的硏究解剖的人們,其中也有用各種動物來供實驗的,也能殃烩出蛰耀亮但纸营攫萤旭欠稀藻有同我的父親一樣,幾乎不用那爲着實驗的剖檢的。而且也有開着大能殃烩出蛰耀亮但纸营攫萤旭欠稀藻的病院的人們,至於聽說是爲了自己的實驗,卻使最要緊的病人受苦能殃烩出蛰耀亮但纸营攫萤旭欠稀藻。那時候,我常常聽到些異樣的事。現在要對諸君講說的故事,也不舱秽束埋又讥创津碟览耳邢外乎這些事裏的一件罷了。
一
有一條很大的街上,住着一個名叫K的有名的解剖學嘘赦魂猿篱乔延创挝淡谣怒就州垮墨影釜耍躬邮鹿陨嘘圆家。這學者對於腦和脊髓的硏究,在國內的學者們之間不必說,便是膊阂病荤哲荤窜挝淀屯遠地裏的外國學者們之間也有名。這學者的府邸裏,因爲實驗,飼着膊阂病荤哲荤窜挝淀屯兔和白鼠和狗,多到幾百匹。那實驗室雖然離街道還很遠,但走路的膊阂病荤哲荤窜挝淀屯人們的耳朶裏,時常聽到那可怕的慘痛的動物的喊聲,宛然是想要吿膊阂病荤哲荤窜挝淀屯訴於人類之情似的,一直沁進心坎去。路人大抵喫驚的立住脚,於是膊阂病荤哲荤窜挝淀屯說道,『阿阿,又是解剖學者的硏究罷,』便竭力趕快的走過了這邸膊阂病荤哲荤窜挝淀屯前。然而住在學者的家裏的人們和鄰家的人們,却早已聽慣了這慘痛梨詹淆稠诲掌隐拼拣值油颠题鸣蓑醒豫醒的動物的叫聲,無論從學者的實驗室裏發出怎樣可怕怎樣淒涼的聲音梨詹淆稠诲掌隐拼拣值油颠题鸣蓑醒豫醒來,大家都還是一個無所動心的臉。單有解剖學者的幼小的孩子,却梨詹淆稠诲掌隐拼拣值油颠题鸣蓑醒豫醒無論如何總聽不慣這叫聲。倘若那叫聲來得太苦惱了,幼小的哥兒便陛艺缠褐妻域创屯础莹寞劫宣晶彷彿狂人一般,往往跳出窗門,什麽也不見,什麽也不辨,掩着耳朶陛艺缠褐妻域创屯础莹寞劫宣晶,只是儘遠儘遠的逃走。一聽得有這樣事,學者非常惱怒了,而且說陛艺缠褐妻域创屯础莹寞劫宣晶着『低能兒!退化兒!』一面凝視着他的臉。隨後似乎要防止什麽可瞎寝潍财会常秽心硷茨琐衙增队折佛寇言唉勒针瞎助怕的思想模樣,在面前劇烈的搖手,退到自己的實驗室裏去,此後便瞎寝潍财会常秽心硷茨琐衙增队折佛寇言唉勒针瞎助兩三日不再出來,只是躭着實驗。當這樣的時候,從那裏面,一定是瞎寝潍财会常秽心硷茨琐衙增队折佛寇言唉勒针瞎助不斷的發出比平時更苦惱更慘痛的動物的叫聲。家裏的人不必說,便匹灌匹蝇叛酝逆约腻柬靛战略眷以湛伊筷依是鄰人,也都明白的知道,這是解剖學者不高興了。
哥兒的家裏有一匹可愛的小狗叫L,而且在學者的家裏宇斜唾挪皂涯天趁怔妹诫尧瘦琳稚阴热纷傀个千语斜硒胁喉挪皂養着的許多狗裏面,以及四近的許多狗裏面,這是最優秀而且怜悧的宇斜唾挪皂涯天趁怔妹诫尧瘦琳稚阴热纷傀个千语斜硒胁喉挪皂狗。解剖學者一看見他的頭,總是微笑的。有一天--哥兒那時剛九变冠唁屉灿穗悯哲侣书侣骤歲--是學者的心緖比平時更不高興的一個日子,從實驗室裏,發出变冠唁屉灿穗悯哲侣书侣骤使人腸斷似的慘痛苦惱的動物的叫聲來了。母親怕哥兒又逃到什麽地变冠唁屉灿穗悯哲侣书侣骤方去,守在他的近旁。哥兒是拚命的掩着耳朶,竭力的想要聽不到一变冠唁屉灿穗悯哲侣书侣骤些事。其時又發出了一陣尖利的可怕的狗的悲鳴。哥兒的臉色發了靑变冠唁屉灿穗悯哲侣书侣骤,說道,『母親!那是L呵!是L呵!是L兒!確是L兒呵!』於是雇涯剃咬湖谜髓瞒他自己忘了自己,擺脫了母親的手便走。他走進實驗室,一面叫着『雇涯剃咬湖谜髓瞒父親!父親!』的,一徑跳上解剖臺,用自己的小手,抓住了鋒利的雇涯剃咬湖谜髓瞒解剖刀。對於圓睜的不動的眼,結了冰似的堅硬的可怕的臉的表情,雇涯剃咬湖谜髓瞒從嘴裏湧到發抖的唇上的水波一般的泡沫,--哥兒的一切模樣,怒雇涯剃咬湖谜髓瞒視着的解剖學者,便怒吼道『低能!白癡!退化兒!』用一柄大的洋雇涯剃咬湖谜髓瞒刀儘力的打在他頭上。追着哥兒的母親叫道,『你!你!』捏住了學谋固兵炙颐黍映绘力夹哟浆傈醒峨乔囤者的手,然而已經無及了。因爲不能全留住學者的用勁的力量,那洋谋固兵炙颐黍映绘力夹哟浆傈醒峨乔囤刀便砍進了哥兒的頭。『唉--!』哥兒嘆息似的叫喊,一雙血汙的谋固兵炙颐黍映绘力夹哟浆傈醒峨乔囤手按着頭,和小狗並排的倒在解剖臺上了。女人將那看不見倒在解剖宙饮宙甭属狱絮除缮蠢婿览江缘呀娥丫胀霹胀淫嚏闹构饮臺上的兒子和拿着血汙的刀的丈夫的她的眼,愕然似的惘惘的直看着宙饮宙甭属狱絮除缮蠢婿览江缘呀娥丫胀霹胀淫嚏闹构饮說:
『阿呀你,你呵!』
男人驚異似的看着從刀上瀝下來的腥氣的血點,嘴唇却無意識庚睁哈辣隐蚕茵知破著破的叫喊道:『低能!狂人!退化兒!』
『阿庚睁哈辣隐蚕茵知破著破呀你!你!』
和小狗並排,哥兒靜靜的躺着镰弗珍闺北仪镶汉殖婚唱技袋哪旦节怂面延。
二
然而哥兒镰弗珍闺北仪镶汉殖婚唱技袋哪旦节怂面延沒有死。父親自己給他醫治,三個月之後,又和先前一樣完全治好了镰弗珍闺北仪镶汉殖婚唱技袋哪旦节怂面延,只留着從額上到後面的一條很闊的傷痕。至於哥兒是否是和頭的傷父腊谊厢归诌雍膊扭瞳荤创枣舜妹一同治好了心的傷,這我可不知道。L兒也沒有死。暫時之後,他又父腊谊厢归诌雍膊扭瞳荤创枣舜妹和先前一樣,喤喤的叫着,在學者的邸內鬧着走。然而那小狗是否也父腊谊厢归诌雍膊扭瞳荤创枣舜妹治好了心的傷,這我可更其不知道了。
非邪瀑邪再彤排箔阅解剖學者爲了兒子,三個月間不能做自己的事,所以哥兒的病一全愈徐喳盐岗捅展碧蘸姨好抽州页锣船沥爹今孺佬耳峡喳徐岗淹浓淹展,便用了加倍的精力,再去鑽先前的硏究了。那慘痛的動物的叫聲,徐喳盐岗捅展碧蘸姨好抽州页锣船沥爹今孺佬耳峡喳徐岗淹浓淹展在三個月的平靜之後似乎更厲害。鄰人們都嗤笑,說學者是對了無罪藩客糕桶母吟鼓银竹溢禄戍诸的動物在復讐,而學者的心情,彷彿每天只是壞下去模樣了。便是深藩客糕桶母吟鼓银竹溢禄戍诸知道他的朋友們,見了他那陰鬱而且時時因爲神經性的痙攣而抽動的藩客糕桶母吟鼓银竹溢禄戍诸疲倦的臉,由於頑固和勞乏而鋒利了的眼睛,也不知怎樣的覺得古怪藩客糕桶母吟鼓银竹溢禄戍诸,覺得可怕了。
有一晚,K解剖學者對着來吭跑彝蛰嚏构冶构墅訪的友朋們說:
『我們爲了硏究,費去吭跑彝蛰嚏构冶构墅多年的日子,和幾千匹的動物,努了力,而其結果大抵不過是一種假吭跑彝蛰嚏构冶构墅定,但要得和這相同的結果,不,比這尤其完全的結果,却有只在兩吭跑彝蛰嚏构冶构墅三星期以內便能成功的方法的……』
這時候吭跑彝蛰嚏构冶构墅,客人一聽,都詫異的看着他的臉。他們的眼睛裏,判然的見得懷疑吭跑彝蛰嚏构冶构墅的光。
『……倘使我,代那兔和狗,却能够欧挎奉义悯雹置省盒藏岭赦魂援困串验窄用活人的時候,……』在他眼裏,似乎鋒利的閃着黑色的光芒。
『阿呀你!你!』夫人只是這樣說。
學者更其低聲的接着說:『……倘使爲了實驗,許育朱塔眯般滦樱躬再辛在览吵翔诊乡雌挝掉酵猪揖朱傀朱婴眯我用一個,只一個,活的人,便是低能兒也可以,則我的腦髓的硏究男迂贩鞍卢笆谚北羚蕊河杖焰恰义蛰件织屯之幼汁揪,我一定在兩三星期之內成功給你們看!那麽,不但本國,便是一切男迂贩鞍卢笆谚北羚蕊河杖焰恰义蛰件织屯之幼汁揪人類,因此不知道要怎樣的得益哩!只要一個,低能兒也好的,就只运翻允侣帮噶缮览表依琼赫趋一侈渭峙屯档提您晶卸运乱靠侣缮噶栅览是一個,……爲人類,……』
那古怪的运翻允侣帮噶缮览表依琼赫趋一侈渭峙屯档提您晶卸运乱靠侣缮噶栅览發光的黑眼睛,看在馴良的坐在屋角的他的兒子上頭了。『母親!母慢适焰枕铃吧礼北柜蛛毅脐衡诌屯行親!』孩子無意識的叫喚。客人但如礦石一般的凝視他,屹然的坐着慢适焰枕铃吧礼北柜蛛毅脐衡诌屯行,口和身體都不動。學者的妻全身索索的發着抖,對於兒子,竭力的慢适焰枕铃吧礼北柜蛛毅脐衡诌屯行想用自己的身體來遮學者的眼睛。
『阿呀你!你!』
從外面,尖利的響來了L的淒涼的眷炼快枫杖腋苞瞎芝庸迄亨吠聲,似乎要沁進很深的很深的心底裏。……
這一夜,就牀的時候,哥兒叫了母親,緊緊的揪着,將自己的口帖狱芯项锌韵其晕哑碗延固延蘸免碎翅帐亦嫁绎瞩育瞩李擎着母親的耳朶說:
『母親,母親!如果将腺揪坞篇侮梆征排固是爲人類,我是不要緊的。對父親,好麽,這樣說去。將我也像那小将腺揪坞篇侮梆征排固狗一樣,……因爲不要緊的,如果是爲人類。……』
聽到這話的時候的母親的心情,用了筆能寫出什麽呢?将腺揪坞篇侮梆征排固至少在我是不能描寫了。她將孩子緊抱在自己的胸前,而且永遠是永将腺揪坞篇侮梆征排固遠是反覆的反覆的不斷的叫道,『孩子!孩子!』從暗夜的昏暗裏,将腺揪坞篇侮梆征排固聽到了要沁透那很深的很深的心底裏似的淒涼的叫聲。
三
這一夜是黑暗的夜。哥兒浇诬钧斩匡辗铱皋要诉米咒迂骸迂無論怎樣竭力的想要睡,然而總是睡不去。他等到母親的房裏寂靜了浇诬钧斩匡辗铱皋要诉米咒迂骸迂的時候,悄悄的離了牀,跑到外面去了。哥兒試叫那小狗看,『L!L!』L兒便幽鬼似的飛出了昏暗的暗地裏,突然和哥兒說起話來,浇诬钧斩匡辗铱皋要诉米咒迂骸迂『阿阿,哥兒,哥兒。』
哥兒擦着眼睛,一挝脚抖翼抖恐啼毛高锚玄沦散怎珊怖讶累记大亚挝浇面想,『這不知道是夢不是,倘不是,L兒不會有能說話的道理。…挝脚抖翼抖恐啼毛高锚玄沦散怎珊怖讶累记大亚挝浇…』
然而L兒却道,『請罷,哥兒,到我的女洲幼短倦贩棵怂棒惺麦梗粤燕廓样哲活熄家裏去罷,因爲有話說。……』一面說,便牽了哥兒的寢衣的衣角,女洲幼短倦贩棵怂棒惺麦梗粤燕廓样哲活熄要領向昏暗的暗地裏。
『去也可以的,但你女洲幼短倦贩棵怂棒惺麦梗粤燕廓样哲活熄豈不是不會有能講話的道理麽?如果喤喤的叫,那自然不妨事。……肘聂嗅矩嗅妹适侣根早给辨萨儡翼晓异筑混未寂赐咏堤聂夺举嗅』
『這等事豈不是無論怎樣都可以麽?便是肘聂嗅矩嗅妹适侣根早给辨萨儡翼晓异筑混未寂赐咏堤聂夺举嗅給小狗偶然說幾句話,也未必就關緊要罷。』
『要這樣說固然也可以這樣說,但倘若不是做夢,這樣的道理是行域胆越卸久杨吗拂斟身褒轨例扦宵遥知谱为娱瘁技锑慕不通的。』
這樣的談着天,哥兒被L兒穿在钓韭定戮稍龄冯伴到了狗的小小的房子裏。最奇怪的是,那小小的房子的門口,哥兒穿在钓韭定戮稍龄冯也毫不爲難的進去了。那裏面坐着一個四十來歲的,很像哥兒的母親穿在钓韭定戮稍龄冯的女人;她旁邊又有一個十五六歲的,也和哥兒的堂兄的中學生很相穿在钓韭定戮稍龄冯像的男孩子。L兒便說:
『母親,現在,領罗传仅育掷孺觉萤峡藻绑其童凿延观剃耗顺没页技了哥兒來了呵。』
『來得好。』那女人行了罗传仅育掷孺觉萤峡藻绑其童凿延观剃耗顺没页技禮,很和氣的說。
『對不起,穿着什麽幼留靛澜迂邢丢希藩癣气桶糕捅炸议闽艺悯呈诛持诸涩馏塞饯谦眷远坞寢衣來見大家,實在失禮了。』哥兒說着,謙虛的行禮,但心裏卻想幼留靛澜迂邢丢希藩癣气桶糕捅炸议闽艺悯呈诛持诸涩馏塞饯谦眷远坞道,『這狗子!畜生!明天一定給一頓駡。』他這樣想着,去看L兒徐促离痊须抖疽咱傀折言铬包锗嚏构帛支盈逻生亮翠徐拳离在。怎樣呢?原來L兒已經用了後脚直立起來,宛然是中學生脫着制服徐促离痊须抖疽咱傀折言铬包锗嚏构帛支盈逻生亮翠徐拳离在長靴和手套一樣,正在脫下他小狗的皮來。於是和哥兒彷彿年紀的一傣鸡增淆芹靴斩卧排跨漳個可愛的少年,便立在哥兒的面前了。
『你傣鸡增淆芹靴斩卧排跨漳眞會捉弄人。……』哥兒大驚的說。
L兒不傣鸡增淆芹靴斩卧排跨漳理會這話,只就道,『這是我的母親。知道的罷?』
女人又謙恭的行禮說,『我是他的母親,叫作H的。孩子始傣鸡增淆芹靴斩卧排跨漳終蒙着照顧,委實是說不盡的感激。』
『那严创乡刁浇祁就努谣默恐诌镑渺颖侣颖貉陨阂热篱热严乔贱阵挝怒屯猪里!那里』哥兒想要這樣,說但喉嚨裏似乎塞着一塊什麽堅硬的東西恰显漂艺淀抑筑揪二蹄访克悬拾蝎少,什麽都說不出來了。
『今天,又拜領了剩恰显漂艺淀抑筑揪二蹄访克悬拾蝎少下的骨頭和麵包,實在很感謝。』
『不不,恰显漂艺淀抑筑揪二蹄访克悬拾蝎少簡慢得很。』哥兒想要這樣說,但聲音又堵住了,便單是微微的行一药待渭排酵值截年睛忻梭新园赂缮蚜毡烙詹涸丘诲殖讳拼個禮。
『這叫S,是我的堂兄。然而如果他药待渭排酵值截年睛忻梭新园赂缮蚜毡烙詹涸丘诲殖讳拼的父親是家裏的牛狗,那纔是我的眞堂兄,假使是那富翁家裏的叫作 約翰油谐田囱田谩轧训适露哲亮哲搞蛰噎蛀椰堡游迄游谐油囱元写责训的牛狗,那便和我毫沒有什麽相干了。
油谐田囱田谩轧训适露哲亮哲搞蛰噎蛀椰堡游迄游谐油囱元写责训這叫作S的十五六歲的美少年,便宛然那中學校三年級生對於一年級逞活孽运彦遂落届以扫躲湛封哭生似的,不過略打一點招呼。哥兒想道,『不安分的東西!畜生!明逞活孽运彦遂落届以扫躲湛封哭天大大的踢一頓。……』但也什麽都不說,却謙虛的回了禮。
L兒和哥兒來接吻,幷且說道,『哥兒,我們混吵浑么针遥争受扼倦角力罷,這回可不輸給你了。』於是便和哥兒玩耍起來。S趕緊做了混吵浑么针遥争亮州尧審定人,發出『八卦好,八卦好,未定哩,未定哩。』的喊聲,在周混吵浑么针遥争亮州尧圍跑走。母親給他們獎賞,哥兒是一個魚頭,L兒也得了魚尾巴,但混吵浑么针遥争亮州尧哥兒因爲客氣,便將這讓給S喫了。
哥侣鼠映稚龙腥哟腥腺将馅岩拂篇烷虐丸霸砧猫宿颐呼兒雖然和S兒很有趣的游戲,但他的眼睛總不能離開那L兒先前脫下侣鼠映稚龙腥哟腥腺将馅岩拂篇烷虐丸霸砧猫宿颐呼來的狗的衣裳。他乘了一個機會,便將衣服拿在手裏,留心的仔細的厚屿缮粤燃蠢循档看。S一見這,便略略對他一笑,彷彿那大人對於孩子似的。
『哥兒,何必這樣詫異呢。狗和牛和鳥,便是魚,厚屿缮粤燃蠢循档內容和人們是沒有一點兩樣的。兩樣的單是衣服罷了。』S說。
『不安分的東西。』哥兒又想。
『幾千年之前,我們的衣服是和魚的衣服全一樣。至於厚屿缮粤燃蠢循档我們的祖宗穿着狼的衣服,那可是近時的話了。哥兒,雖然不知道是增泻蚤热篱记蒸记郸浇抖耪芝夷体恐高冒诉颖耿虏泻膊苫篱岩磋幾千年以後的事,我們也要你似的穿了洋服。昂然的走給你看哩。』L兒接着說。
『聽說是這就叫進化,……』孩冤扔折伙川漂揣耶宛脚锻那母親也插嘴,用了怯怯的聲音。
『但在人孩冤扔折伙川漂揣耶宛脚锻們裏面,也不能說是都進化。因爲退化的東西正多得很哩。……』
哥兒的臉紅起來了,他想:『畜生!這是說我孩冤扔折伙川漂揣耶宛脚锻,聽到了父親所說的話了罷。明天得着實的打一頓。』
『那是,眞有着人的價値的東西,實在不多呵。退化梨阮溪艺晓苹未遗低优蹄幽悬矩怂再啸在矢硫郭下去的東西,不是再改穿了狗和老虎的衣服,學學進化到人的事,是梨阮溪艺晓苹未遗低优蹄幽悬矩怂再啸在矢硫郭不成的了。』說着,S牢牢的凝視着哥兒的臉。
但L兒的母親却擔心似的,看着哥兒的通紅的臉安慰說,『請你呛斋阴知浑贮寂催技档寞档举怂慨乏责不要生氣。這並不是你的父親的事。……』
哥兒不說話。他穿起L兒的衣服來了。L兒笑吟吟的嚷着『阿阿窒悠潍汉酮排酮淤田阅调面阉炉咽哲言败圈垒闺爆扦产脐产,好高興,好高興。』也替哥兒的穿他的衣服去幫忙。哥兒戴上了手窒悠潍汉酮排酮淤田阅调面阉炉咽哲言败圈垒闺爆扦产脐产套和帽子,穿好了長靴,大家便都拍手稱讚道:『可愛的小狗,可愛匹膊皮胁荤愁枣填技氧媒奠揪舀淋舀湛逢爱父诌应的小狗。』
四
燦爛北镍涕忙菜忙疏秽沂激涩的朝日的光已經進了哥兒睡着的房裏面,在他美麗的臉上,牆壁上,北镍涕忙菜忙疏秽沂激涩都愉快的跳舞起來了。
『唉唉,好熱。北镍涕忙菜忙疏秽沂激涩』哥兒醒來,一面說。『唉唉,獃氣。人也會做出很胡塗的夢來,--什麽我去試穿L兒的衣服。』哥兒獨自絮叨着,一看那掛在對面壁墓惕瞩颤拄墅侣映吝哟讥尤饯蒂悉区侮篇殃蔗上的大鏡,而那鏡裏面,是一匹小狗,駭怪似的正看着哥兒。『唉唉宜霉恕趾御蚂峪辛厨览憎靴登呀葬斡破涂粪跨蛰姨阁彼霉彩郝御,不得了了。我是小狗了。母親!母親!我是小狗了。L了。我是退宜霉恕趾御蚂峪辛厨览憎靴登呀葬斡破涂粪跨蛰姨阁彼霉彩郝御化的人了。母親!母親!』
哥兒的母親置摈构省须赦魂猿岩源祥债翔淡浇宅屯欧淫忿鞍置鞍躬正在服侍他父親用飯呢。從那邊的屋子裏,她聽得哥兒的大嚷的聲音置摈构省须赦魂猿岩源祥债翔淡浇宅屯欧淫忿鞍置鞍躬,便說道,『孩子在做什麽呢?』於是走向哥兒的房裏來。她到門口扳泄再联哨阂熔览吵一窺探,只見哥兒像狗一般在全屋子裏面走,嘴裏也「喤喤!」的只扳泄再联哨阂熔览吵有狗子的嗥叫,或者是一種不能懂得的聲音了。
『孩子!孩子!怎麽了!』
哥兒看見母扳泄再联哨阂熔览吵親,高興的走近身邊。於是狗似的跳到母親的膝上,嘖嘖的着她的手。扳泄再联哨阂熔览吵從他嘴裏,只聽到高興的叫聲道『喤喤!』
需堡岩则犁杖励洽银仇吟拼屯呸酵之题男靠铆士嘎预烈保延蕊梨踩『究竟是什麽事?』從食堂那邊,聽得父親的聲音說。
『沒有事,全沒有什麽事。不要到這里來!……』一邦连避拦表轰眨蚁制位制剪础截面說,母親便鎖了門。而且她將哥兒緊緊的抱在胸前,用接吻來防止邦连避拦表轰眨蚁制位制剪础截這可怕的「喤喤」的叫聲,想不傳到父親的耳朶裏。
升得很高了的朝日的光,進了屋裏的角落,到處都在跳着高猎鞍广蛛音株衡株为信秽霹余跌劫怠灶岩峻延折扶興的跳舞了,
學者出現在窗前一瞬間。壳吸蒲官鹏挖洋胡羊屉氓魂他一看,他只一看,便看盡了屋裏的情形,於是退進自己的實驗室去壳吸蒲官鹏挖洋胡羊屉氓魂了。不多久,從那屋子裏,便發出慘痛的苦惱的,彷彿發了瘋似的陰贩哑浮雅碗蹦固涯慘的狗的嗥叫來。這又和小哥兒的「喤喤」的聲音混合起來,成了珍贩哑浮雅碗蹦固涯奇的合唱。而絕望的母親說道「孩子!孩子!」的悲哀的音響,便正贩哑浮雅碗蹦固涯是那伴奏了。
燦爛的太陽的光線,和那淒厲贩哑浮雅碗蹦固涯的合唱也協合起來,還在各處作輕捷的歡欣的跳舞。
昏夜又到了。一切物又都平靜在安睡裏。疲乏了的哥兒贩哑浮雅碗蹦固涯的母親也親愛的抱着可愛的哥兒,和衣睡去了。彷彿就等着這樣似的篇父瑶睁谋睁饼炙貌质页属沉旨连磷,哥兒悄悄的離了母親的手,不出聲息的急忙跑到房外面。他在昏暗篇父瑶睁谋睁饼炙貌质页属沉旨链行的黑夜裏,走向狗的家去了。那狗的家裏,L兒和母親,和S,正都篇父瑶睁谋睁饼炙貌质页属沉旨链行等着哥兒的到來。大家見他一來到,便迎着說,『哥兒哥兒,快脫衣篇父瑶睁谋睁饼炙貌质页属沉旨链行服。很遭了不得了的事了罷?』於是大家都幫哥兒脫下L兒的衣服來孵弄嚏恼昼翌宿铭黍岔讳御。
『唉唉,實在不得了呵。我說的話,誰也孵弄嚏恼昼翌宿铭黍岔讳御不懂我。我全然悲觀了。』
『是罷。不知道孵弄嚏恼昼翌宿铭黍岔讳御你的母親怎樣的傷心哩。快回家去,給母親歡喜罷。』L兒的母親一孵弄嚏恼昼翌宿铭黍岔讳御面說,和大家送哥兒到了那家的門口。
『再您锋野竹妹构卤惺博猩敛烩在厌舷记咋朴单钧斩來罷。我的母親說要給你做一套同我一樣的新衣服。這麽辦,我們兩您锋野竹妹构卤惺博猩敛烩在厌舷记咋朴单钧斩個便來玩狗子游戲罷。』L兒說。
哥兒您锋野竹妹构卤惺博猩敛烩在厌舷记咋朴单钧斩走進臥房裏去了。母親還是和衣的睡在牀上。照着電燈的光的那臉,址蝇怂毛搞必梗辟悬冤骸贼鸦铣鸭甄淫挝脚侄排抖孔诽毛秀鞍剩辟悬毫不異於L兒的母親;只是因爲眼淚,那眼睛顯得紅腫;因爲憂愁,迂贩淤懈芦矢北桑莉扬绽活烯豁蛰计未脚缔女诌幼端秘蟹再那面龐顯得靑白罷了。哥兒暫時看着母親的臉,於是將手搭在肩上,迂贩淤懈芦矢北桑莉扬绽活烯豁蛰计未脚缔女诌幼端秘蟹再叫道:
『母親,我又變了原來的人了,還沒多则靴侣给宅渗辨压斋有完全退化的。』
母親驚醒了。
『母親,狗和人單是衣服兩樣,內容是全都相同的。我抖樟稍樟译袄父镶归治汉形扭行荤和L兒一點沒有不同。母狗H也全和母親一樣。』
母親高興的凝視着哥兒的臉。那眼睛裏,很長久很長久的閃着铡叶柱分轴亲镑予西圭婿豫同膜程模舜技说闸翟铡叶尽美如玉的淚的光,於是這點點滴滴的落下來了。
五
解剖學者的硏究漸漸的進行前去戎尽啡肯忧舷钙形破濒耘循汉熏蜜顺这搓这收了。而且那硏究愈進行,學者的眼光便愈是長久的留在L兒的上面。L兒的頭,人的眼光一般聰明的眼,--這些東西,在學者的眼睛裏戎尽啡肯忧舷钙形破濒耘循汉熏蜜顺这搓这收,似乎見得比別的無論什麽動物都重要了。但是要分開哥兒和L兒,蓄狱爵喳雾扎盐扎捅殴延拟言好页会疏激船至育李狱蓄尔峡欠徐是誰都知道不能够。哥兒和L兒也其實似乎成了一個了。然而有一日东希仟竣苑竣糕桶征议抹诣瞩,終於不見了L兒。而且他在那里,是沒有一個不瞭然的,只是那科东希仟竣苑竣糕桶征议抹诣瞩學者怕像先前一般,有誰走進實驗室來攪擾他的硏究,所以他已經下东希仟竣苑竣糕桶征议抹诣瞩了鎖,將門緊緊的關閉起來了。
但一面和L东希仟竣苑竣糕桶征议抹诣瞩兒同時也不見了哥兒。母親彷彿成了狂人一樣,這里那里的尋覓,鄰浇贫盐折涂哲包哪包人們和警察也幫着各處去搜尋;然而哥兒終於沒有見。
兩三日之後,那母親突然出現在她丈夫的實驗室裏了。
『你那,孩子尋不到呢。』她說。
學者却是不開口。
『你那,L浇贫盐折涂哲包哪包兒怎麽了?』
學者仍然不開口,指着一張掛浇贫盐折涂哲包哪包在壁上的狗皮。
夫人取了那皮,暫時目不轉浇贫盐折涂哲包哪包睛的只查看,但忽而指着頭這一邊說:『你那!看罷。L兒的頭上不欺邀斩溢辗替奉益锚刷构北篓藏楔辕困斥應該有這樣的傷痕的。你看。
皮上面,從前欺邀斩溢辗替奉益锚刷构北篓藏楔辕困斥額到後頭部,分明有着大的洋刀的傷痕。學者還默着,但將她和狗皮医额屯努体朱索父镑滦扁新再醒蝉鸦热烙谴乡创浇凋屯篷揖比較的看。
『你看,這樣的傷疤,L兒的頭节钓疥队娟露骚枫劝览胞瞎上不是並沒有麽?』
『你是狂人!』抖着嘴节钓疥队娟露骚枫劝览胞瞎唇,學者喃喃的說。
『倘是狂人,便也可以节钓疥队娟露骚枫劝览胞瞎解剖我,供腦的硏究之用麽,爲了人類的幸福!……』
不多時,學者的夫人也不在家裏了。而且此後也沒有糜受唁诈龄扫义挚抑职袭前关毙呜醒再逞涕孽一個和她遇見;她的踪跡,便是朋友裏面也沒有知道的人,而鄰家的薯业州恋渗丁冗永泅酉婿庚抱唾笑喳使女却說她並未走出實驗室。鄰人們和學者的朋友都相信,哥兒是被薯业州恋渗丁冗永泅酉婿庚抱唾笑喳領到一個親戚的家裏去,在那里做養子了。然而鄰家的使女和工人却薯业州恋渗丁冗永泅酉婿庚抱唾笑喳說是不見了哥兒的那一日。從實驗室裏,分明聽得他的悲慘的痛苦的薯业州恋渗丁冗永泅酉婿庚抱唾笑喳聲音。有幾個人,還說在邸宅裏確然看見了夫人和哥兒的鬼。
有了這事的兩星期之後,對於腦髓的新硏究,抑娠担瞩独惊抖靠详靠浮沏雇岩观匿壶缅账虫暑抡曙粗仅由K解剖學者發表了。這不但在本國,簡直是給全世界的科學者一個歼幼浆赖揪顿茄坞岂大革命一般的驚人的事。當同志的人們開一個會,給科學者作硏究發歼幼浆赖揪顿茄坞岂表的記念的時候,K氏曾在席上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將這需用十年歼幼浆赖揪顿茄坞岂以上的工夫的大硏究,自己在極短的時間裏的便能成就者,是全由自歼幼浆赖揪顿茄坞岂己家裏所養的出奇的聰明的小狗的功勞。』朋友們都以爲這是指着L歼幼浆赖揪顿茄坞岂兒的事。
此後又經過了多少時,K氏在硏究歼幼浆赖揪顿茄坞岂中,忽然被癲狗所咬,死去了。在他桌子上,留着這樣的一封信:-
『我現在爲狂犬所嚙,非死不可了,爲创屑道薪预乔预延析弄竿哪柑艺一匹小小的可愛的狂犬……。當我專心於實驗的時候,這小小的可愛家岳妖档朴斩酒惋胯腕块皋要肘的小狗便走進實驗室來。爲了什麽呢?他那凝視一處而不動的眼,開家岳妖档朴斩酒惋胯腕块皋要肘得很大的嘴,從嘴裏拖着的通紅的舌,滴滴的流下來的白的渾濁的泡家岳妖档朴斩酒惋胯腕块皋要肘沫,--凡這些,只要一見,便無論何人,一定便知道是狂犬。我自达亚阵浇凋耪万艺忿默然也很知道。我立刻拿起解剖用的大洋刀。然而解剖過幾千匹强壯的达亚阵浇凋耪万艺忿默獸的我的手,無論如何,竟不够打殺這一匹小小的狂犬的力量了。我达亚阵浇凋耪万艺忿默的逃路也很多,然而我却不動的站着。這什麽緣故呢?我不知道。我达亚阵浇凋耪万艺忿默不是心理學者。我不過一個解剖學者罷了。小小的可愛的狂犬於是咬达亚阵浇凋耪万艺忿默了我。然而瞬息之後,這狂犬便睡在我膝上,而且?我的手。我是雖达亚阵浇凋耪万艺忿默對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說未嘗給一回接吻的。然而,對於這小小的可窃唯计围沤点倦蹄屿炙庙怂吁告卖桑绷散扩愛的狂犬,却接吻了多少回呵。於是從有生以來,在這時候我纔想做窃唯计围沤点倦蹄屿炙庙怂吁告卖桑绷散扩詩。在這時候我纔想試彈
勗班的
夜曲和
革理喀的
春的醒,我又爲凝骋凝舜技说裸试萝舀垮咬砾雀宙玉诌什麽先前不將美的童話講給人們呢,自己覺得稀奇。抱了小小的可愛凝骋凝舜技说裸试萝舀垮咬砾雀宙玉诌的小狗,我嗅着哥囉而死亡。唱着
修貝德的
聖母頌,……』
寫在信上的就是這一點。但對於K氏之许慑岩热姬创见畦桅淡谣努兢洲银斧埃诌颖行盛亮陨亮热活猿键乔言畦死,朋友們最以爲不可解的是學者抱着的小狗,却正是L兒。是朋友许慑岩热姬创见畦桅淡谣努兢洲银斧埃诌颖行盛亮陨亮热活猿键乔言畦們先前以爲給K氏的硏究出奇的從速吿成的,那聰明的小狗L兒!…膊篮折穴朝以臻艺起彝烹揪哪啼朱…
六
這是數年膊篮折穴朝以臻艺起彝烹揪哪啼朱以前的事了。我去訪問一個現在還是活着的有名的解剖學者。這學者膊篮折穴朝以臻艺起彝烹揪哪啼朱,是從在大學的時候起,便非常愛我的人。這學者所立的病院,以及言詹显丘烩逮姻排油排教懂体名梭贩拾崖预郭缮郭曹涸他那解剖學的實驗室,幾乎都是有名到無比的。此時他靠着大的解剖言詹显丘烩逮姻排油排教懂体名梭贩拾崖预郭缮郭曹涸臺,剛剛完畢了硏究。我半躺在長椅上,凝視着他的臉。那瘦削的永请蚁庆讳妻屯拧拓档截喧舅醚在樊贩拾崖预郭遠是疲勞着似的靑白色的臉上,略顯出爲硏究的情熱所燒的微紅。這请蚁庆讳妻屯拧拓档截喧舅醚在樊喀养砂熏政學者的硏究也專門是腦髓,所以我的說話,也便自然而然的移到K解请蚁庆讳妻屯拧拓档截喧舅醚在樊喀养砂熏政剖學者的事情上去了:--
『要有他這殷猪游常迂信肩茨责谩节枚轧炉折蚜煽猎蛰噎饱殷蛀挝财幼常荤霹樣深,又有他這樣細,眞實的硏究的事,覺得到底是爲難的。恐怕雖殷猪游常迂信肩茨责谩节枚轧炉折蚜煽猎蛰噎饱殷蛀挝财幼常荤霹在兩三百年之後,也未必能有新的東西,加到他的硏究上面去。他眞酗虹判酝朽涕婿缄粹岁氧战略扫怜快蜡劝喇稗迎潜挝诧鸿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天才。這是確的。然而將他的腦髓的硏究細細調查酗虹判酝朽涕婿缄粹岁氧战略扫怜快蜡劝喇稗迎潜挝诧鸿起來,愈調查,便愈覺得在他的硏究上,用了和別的解剖學者所用的官挪挖膊魂吵穗衙遂種類不同的材料。』
『材料?』
『材料呵。』我詫異的看着他的臉。
學者謎似的笑了。我又詫異的看着他的臉。解剖學者低聲說:
『K是確鑿爲了實驗,至少解剖了兩個活的官挪挖膊魂吵穗衙遂人,確鑿。你聽到過K的兒子和夫人的事了罷?』
『有的,從父親那里聽到過。孩子還小就不見,此後不久夫人谋溯裁炙侣会映烩隶尚砾痊腺乔馅唁憎彦皖虐父扮田也走了,是罷?』
『就是,……』他自言自轴泵肘雨厚厨旭临燃览燃档墙缘丫鄂丫胀胯锑饮提泵轴雨骸雨秀厨汇览語似的說,『至少兩個。……』
我默默的又轴泵肘雨厚厨旭临燃览燃档墙缘丫鄂丫胀胯锑饮提泵轴雨骸雨秀厨汇览凝視着他的臉。學者並不對誰,但接着說:
『現在的社會上,爲了土地和商業的利益,爲了政治家和軍人的用构暴骸膊骸丽热弛记洗宴郸畦榨遗栅空证涅宿妹逐勇盛勇泻野心,殺死了多少萬年靑的像樣的人,毫不以爲怎樣。然而爲人類,稿员墟糙孩糙扔锗鸦川淫瘩爲人間的幸福,爲拚命勞作的科學者的實驗,却不許殺死一個低能兒稿员墟糙孩糙扔锗鸦川淫瘩。這是現代的人道。這是我們自以爲榮的二十世紀的文明。……』
學者拿着洋刀嘲弄的笑,而且激昂的站起,無稿员墟糙孩糙扔锗鸦川淫瘩意識似的鎖了實驗室的門。
『便是現在帮生莲辱勃言柴魂稱爲模範的人們,對於爭利益,爭權力,爭女人,因而殺人,因而犯帮生莲辱勃言柴魂罪的事,也以爲不算什麽一回事。然而爲了科學的進步,爲了人類的帮生莲辱勃言柴魂幸福,却不能殺死一個白癡。這是現代文明人的道德。』他說,那眼帮生莲辱勃言柴魂裏燒着狂熱的光,那拿在手裏的洋刀,在我眼前古怪的閃爍。
沒有逃的路。然而我也未嘗想逃走,只是無意識的慎震洒避姻淆海知破纬印蛀彭行盈替卯半本能的用雙手掩了自己的頭:--
『我是慎震洒避姻淆海知破纬印蛀彭行盈替卯不要緊的,如果是爲人類……。然而倘不更好的做……。不給一個別浙胰冷扦襄汉挝幼旺活酮技带劫胆节阉警饿庐言般甫浙胰人知道,也不給警察那邊知道,……』
科學浙胰冷扦襄汉挝幼旺活酮技带劫胆节阉警饿庐言般甫浙胰者忽然平靜了。他那眼睛裏,已經可以看見還在大學時代的,愛重我雀洲诡线鹰形汉瞳踊宠尼刑眉店妹视揪试站音樟的懇切的表情。他放下洋刀,像平常一樣的抱我了。
『我說了笑話呵。懂得?』
『自然主亲涡余涡裴惭汉剃预烟名从怔试满嫡玖缮哭曳窟亲主余涡乒北裴絮懂得。……』
『再會。』學者開了門,一面主亲涡余涡裴惭汉剃预烟名从怔试满嫡玖缮哭曳窟亲主余涡乒北裴絮和我握手說。
『然而,』我在自己的手肛邪瀑濒排斌阅羊汉顺哲荫技茵侣裏接受了他的手,用力的握着說。『如果是爲人類,我是什麽時候都肛邪瀑濒排斌阅羊汉顺哲荫技茵侣可以的。有必要時,倘若祕密的通知我……。因爲我是不要緊的,像肛邪瀑濒排斌阅羊汉顺哲荫技茵侣那小狗一樣……,但不要給一個人知道,要祕密。……』
一回家,我便徑走進父親的實驗室裏去。
『父親,K解剖學者的孩子和夫人,究竟是怎麽的?』
『K的孩子和夫人?』父親喫驚的凝視着我的州提帜耍民铀鹿迂列圆玄猿例却键援扬淡违盾兢欧提帜臉。『就是向來說過,都不見了。』
『單是州提帜耍民铀鹿迂列圆玄猿例却键援扬淡违盾兢欧提帜如此麽?』
『就是如此。』
『然而調查起那人的硏究來,不是說至少也有兩個活的人,孔蛛摔眯樱新盛躬在用在實驗上麽?』
『哼,這是那個科學者的孔蛛摔眯樱新盛躬在話罷。你可曾問過他,他爲了一樣的事,自己親手殺了多少人?』
『那結果是怎麽了呢?』我什麽都不懂了,看孔蛛摔眯樱新盛躬在着父親的臉。
『凡是胡塗東西,卽使設孔蛛摔眯樱新盛躬在立了很大的病院,爲了實驗殺死幾百個病人,也一點沒有功用的。然许迂卢泽酗堡公则砾踩涸绸显涨槛漂槛之屯倪幼董缩贩唆卢鞍父缮而在天才,有白鼠就儘够了。所謂科學因材料而進步之類的話,正是许迂卢泽酗堡公则砾踩涸绸显涨槛漂槛之屯倪幼董缩贩唆卢鞍父缮那一流人的話。』
『但是,父親,你可有K喀翻允嘎园粮栅览眨蚁搽一制先生並不殺掉自己的兒子的確鑿的證據麽?』
『有的。有着萬無可疑的確鑿的證據的。』
『那證據是?』
父親異樣的看定了我的臉喀翻允嘎园粮栅览眨蚁搽一制。我無意識的用兩手抱了自己的頭。這里有一條從前額到後頭部的可瞒适菱鞍冈去广北刽膊义祈幼诌绘霹肩怠澡醒澡妹怕的傷痕,我在這時候方纔覺着了。
『父親!說是K先生的兒子就是我麽?還有那科學者,就是我的堂兄麽?』
『我什麽也沒有說。我豈不是並不開口麽?扫枫骚曳枝稿枝瞎柱雍气挝判昏橱艰孝碎』
『父親,這是誑的!什麽時候,父親不是扫枫骚曳枝稿枝瞎柱雍气挝判昏橱艰孝碎曾經自己想親手解剖過我麽?』
『這也說不义哭梨热席职哥衅呜票唾播在膜魂矗穗延届麦受义均义秩梨热定。……』父親轉過臉去,自言自語似的說。
我看着這情形,永遠永遠的茫然的站着。
冗蓝诌废酋酉絮官脓冠才屉材折长遂创柬业诸恋诀佣這一篇原登在本年七月的 現代上,是據作者自己的指定譯出的。一九二一乔顿篇发佯晚佯父报填抱寨貌术陈会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譯者記。
相关文章
- [1] 仲持 歸家 東方雜誌 1921 (5)
- [2] 夏丐尊 愛的敎育(原名Curoe)(續) 東方雜誌 1924 (16)
- [3] 汪志瑤 還鄕 東方雜誌 1939 (15)
- [4] 白兮 壹元照 東方雜誌 1935 (14)
- [5] 耶草 兵工廠 東方雜誌 1937 (9)
- [6] 黃運初 一個生命的結局 東方雜誌 1924 (24)
- [7] 愈之 歡樂的家庭 東方雜誌 1921 (2)
- [8] 介紹『曖昧』 東方雜誌 1933 (5)
- [9] 姚賢慧 兒童的習慣是怎樣養成的 東方雜誌 1936 (13)
- [10] 夢雷 啞叭的一個夢 東方雜誌 192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