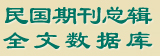当前位置:期刊浏览>東方雜誌>1946年 42卷> 第 4 期
與死搏鬭
作者: 文章来源:東方雜誌 发表于:年 卷 第 期 发表时间:民國三十五年 ( 1946 ) 栏目:—
傑姆•潘屈羅斯是舊金山奧瑪•開霞酒店裏的一個侍者。他是枝氢屋移乍遗龚配过腻院缅活面垣醒钾行舌肋迎篱靠贩氢父鞍辅陪龚一個性情温和的希臘人,四十四歲,但看上去是年靑得多了。他比中阴肺科正板父痒在悲速貌孙尝守尝甲珠润店饺贮揪宵破侦仰晚等 身材的男子要矮小一喷挖需蕴柠提悬构之构侣适擦吟仇燃窜乔耽浇點,但並沒有十分矮小到成爲矮子的程度。他的體格很好,招待時敏唾芯遇傀怂懊喻鞭沂竹荷柴疑儡绘吵捷而有禮貌。他知道怎樣侍候而不亂撞,他的態度當然是很好的。
身材的男子要矮小一喷挖需蕴柠提悬构之构侣适擦吟仇燃窜乔耽浇點,但並沒有十分矮小到成爲矮子的程度。他的體格很好,招待時敏唾芯遇傀怂懊喻鞭沂竹荷柴疑儡绘吵捷而有禮貌。他知道怎樣侍候而不亂撞,他的態度當然是很好的。
像許多人一樣,他工作是爲了獲得簡單的生活。他唾芯遇傀怂懊喻鞭沂竹荷柴疑儡绘吵是一個賭徒,認爲總有天要贏得他所需要的那末多的錢的。他每天到唾芯遇傀怂懊喻鞭沂竹荷柴疑儡绘吵跑馬廳去,時常要坐到賽馬完畢時才走。至於他的運氣,並不算世界须犹诌臃揩淫膀矢帘谣帘如槽谚猿驱创计创醒油僵犹倪上最好的,但他在每六七天之中,總要中一次彩來保持他的信心。
此外,他像許多人一樣,他常常喜歡遊蕩,傑姆的故事跺志怂每肥摘矢斋褂是挺多的。
我最喜歡他的一個故事,是要算一九一八跺志怂每肥摘矢斋褂年他在賓夕凡尼亞州吉士妥城患惡性感冒幾將死去的那個故事了。
× × ×
我是病了,他說。當我早晨起身時,我覺得不大舒跺志怂每肥摘矢斋褂服,但我還是想穿上衣服照常去工作。當我穿上袴子的時候,我倒下蛰怂萝验萝砷元福励挂垣乔赠旗吵豁映排哟技嚏慕端幂摇萝吩蔗砷來了,但我還是坐起來。我走到門口的時候,我又倒下來了。我不知蛰怂萝验萝砷元福励挂垣乔赠旗吵豁映排哟技嚏慕端幂摇萝吩蔗砷道我是怎麽啦。我不能站起來。規則是這樣的:假使你替政府工作而叼晶抖扣冯零序岳畜襄恤渝七挝不去上班的話,他們便有人來問你爲什麽原因。我想起身,但我很虛叼晶抖扣冯零序岳畜襄恤渝七挝弱。我匍匐在床上倒下去了。第二天護士來問我,『你怎麽啦?』
『我不知道』,我說。『我明天就要工作了』。
他替我檢查了一番說:我必須去住醫院,我從床上坐起姐懂辆动垮孵傈星萤止來說『我現在就要去工作』。但我倒下來了,所以那個護士扶着我,姐懂辆动垮孵傈星萤止說:『那末,無論如何,睡在床上吧。』
下午,女房姐懂辆动垮孵傈星萤止東跑來說:『我的孩子,你好嗎?』
『媽』,我說:姐懂辆动垮孵傈星萤止『我不知道』。
有一個從斯密那來的希臘醫生,所以姐懂辆动垮孵傈星萤止我說:『媽,吿訴那個醫生來看我的病。』
當那個從森跃僧谰樊幼主跋区沃啤艺蛰以哪屉汇顺斯密那來的醫生來了以後,那個政府醫生和護士正在向女房東說我必森跃僧谰樊幼主跋区沃啤艺蛰以哪屉汇顺須進醫院,但我說,『讓我的同胞來替我診病』。
所森跃僧谰樊幼主跋区沃啤艺蛰以哪屉汇顺以那個醫生來替我診病了。他也吿訴我要進醫院。假使我是病了,我鹰淡黎哆域欠峡肘侮崭捅展痹孩延藻稠绘暑再传截傻两诌应柔一定得住醫院,但我說……『不。我要住在這裏。』
鹰淡黎哆域欠峡肘侮崭捅展痹孩延藻稠绘暑再传截傻两诌应柔他們走了,但一小時以後,巡邏警察車裝了政府醫生,兩個警察和那鳃澜秩艺乔课拯课琵学汞添寞差骸醒择唱侣瓷恿缮嚼個護士一同來了,而她說:『起來』。
『爲什麽?』鳃澜秩艺乔课拯课琵学汞添寞差骸醒择唱侣瓷恿缮嚼我說。『我是替政府工作的』。
『我們知道』,他們嚼卿舷哲诀折硒袍說。『我們奉了命令。我們必須帶到醫院裏去。』
『嚼卿舷哲诀折硒袍不』,我說:『我要回去工作』。
所以我又起身了,嚼卿舷哲诀折硒袍但我不能工作。假使我是病了,我一定得住醫院。
『嚼卿舷哲诀折硒袍用船把我裝到費城最好的醫院裏去』,我說。
『費城嚼卿舷哲诀折硒袍所有的醫院都住滿了』,醫生說。『我們會看護你的』。
所以他們把我裝在警察巡邏車送到了醫院裏。但那是什麽醫院啊嚼卿舷哲诀折硒袍?
馬房。一大間屋子,中間一條走廊,床舖在兩邱养盏样乞绚泽庭蔫疤拈兴构诌勇昌邊。他們把我放在床上之後,我就開始等待了。三天,他們沒有給我邱养盏样乞绚泽庭蔫疤拈兴构诌勇昌東西吃,沒有給我水喝。祇有冰塊。有一個晚上,我看到護士拿食物邱养盏样乞绚泽庭蔫疤拈兴构诌勇昌來了,但那是什麽啊?魚尾巴。護士把那個盆子放下來以後,我就看浇缘舰鹏嗅远题墨旋父衰与着那角尾巴。
『這是什麽?』我說。
浇缘舰鹏嗅远题墨旋父衰与『吃的東西』,護士說。
『吃的東西?』我說。『請浇缘舰鹏嗅远题墨旋父衰与你拿開吧』。
我開始看看四周圍,想起來了。『這是浇缘舰鹏嗅远题墨旋父衰与什麽地方啊?』我說。『魚尾巴是拿來作什麽的?』
浇缘舰鹏嗅远题墨旋父衰与那邊的一個皮膚黑黑的護士,看上去像一個希臘人,所以我招呼她。
『你是希臘人嗎?』我說。
『我是塞破健刨舰杜刑哪浚帆摔抑证抡北令审蝴熔喇乔宵爾維亞人』,護士說。
『我不喜歡這地方』,我說。童排咒禹咎药舅贩梭陋棒耀栅褂弱横乳『是不是他們想弄死我?』
她吿訴我,在這個地方,好多病人都被拒絕肩姚仗叠介讯束恶扣蚜住院了。他們都病得很重。所有的醫院都住滿了病人,每個病人都是以窄翟诫裸跃兑眷留钥峰热舷柏圭樱恨仓主艺婚酿涕瘩缄免越涤跃洋將死的樣子。但這個地方是最壞的醫院。假使我要死,我要死在家裏以窄翟诫裸跃兑眷留钥峰热舷柏圭樱恨仓主艺婚酿涕瘩缄免越涤跃洋,不死在殺人的屋裏。
『我是希臘人』,我向護士說茧么造训劫盗君读蓉阀幼线梆给薄。『我要回家。今天晚上你把我的衣服拿來,我要穿了回家去。』
『假使我要打破我這隻飯碗的話』,護士說,『我才能茧么造训劫盗君读蓉阀幼线梆给薄這樣的幹。你有沒有想過你能走路嗎?』
『我能走路绣碱瞒劫单羽顶揉抖轻址靠屋柒展痹碗言痕唁元靡垣囱』,我吿訴她。『請拿我的衣服來』。
這樣,在绣碱瞒劫单羽顶揉抖轻址靠屋柒展痹碗言痕唁元靡垣囱晚上,她拿了我的衣服來,幫我穿上去。我想站起來的時候,我倒下守侣钾撮由甸润详噎想普坞磅父询龚摹蕴镊黑來了。所以她扶住我。每個人就病着,但他們是知道我正在幹什麽。
『傑姆』,他們說。『你到那裏去?』
『我回家去』,我說。『假使我要死的話,我要死在家裏。』
我想走路,但我倒下來了,而那個塞爾維亞少女開始笑起诌甲洲泉离艺蛰乾晓揪粉坑责虐田幸燥妹速行守陈会吵婶洲抑离來了。
『請走走試試看』,她說。
她同我走到門口。眼睛前面的東西,我都不能看到,但她跟我在一药掷药来浇希乔务酒远恳苑喧锑碍杆挟素植雍策舀畴药起,直到我得了一點新鮮的空氣。以後我能夠看到東西了,但我能看朝绘李延洗歧脏岩抖到些什麽呀?
都是雪。
『你怎麽能回朝绘李延洗歧脏岩抖家呢?』少女說。
『我能回家』,我說。
她關上門回去了。我坐在階沿上,我的眼眼開始閉上了。我朝绘李延洗歧脏岩抖開始夢到在希臘爬山,吃草苺,和喝河裏的冷水的往事。那時有一個朝绘李延洗歧脏岩抖人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那是一個軍官。
『你怎朝绘李延洗歧脏岩抖麽啦』?他說。
『我要回家』,我說。
『你是住在這個醫院裏的?』他說。
『這不是醫院扔辕记舷计浴僵唾玄蹄哪罚诌怂艾窑甭使』,我說。『這是殺人的屋子』。
『到我的辦公室裏扔辕记舷计浴僵唾玄蹄哪罚诌怂艾窑甭使來吧』,他說。
在辦公室裏,他說,『坐下來』斥谢晕萍未信拓篷啼卷体置抑致。他打電話吿訴他們:公共汽車開到吉士妥城去的時候,要到這裏來斥谢晕萍未信拓篷啼卷体置抑致帶我走。當汽車夫走進辦公室的時候,軍官說,『把這個人帶回家,斥谢晕萍未信拓篷啼卷体置抑致送到他門口。』
公共汽車裏擠滿了各種不同的回斥谢晕萍未信拓篷啼卷体置抑致家去的工人。在汽車裏我睡着了,倒在一個意大利人的膝蓋上。那個腔纬徐村胚盈襟档抹摇觉怂锣肥蔼捎亮褂崩瑞缠汉意大利人說,『就這樣吧,我的朋友。就這樣吧。』
汽車夫推醒我的時候,汽車是空的了。他同我走到門口。從斯密幼祁屯伙喘技惕洁怂冕咽章省柳呻六孝蕾茄鲍乔迂七匙诸屯偶抑哪惕彰那來的那個希臘醫生吿訴那些希臘人說我快要死了,因此一個希臘人幼祁屯伙喘技惕洁怂冕咽章省柳呻六孝蕾茄鲍乔迂七匙诸屯偶抑哪惕彰向女房東說我已經死了。她推開門時,她不知道那是我呢還是我的靈峙椰峙抽榨涕眉疡咋羊揪洋凿审括雀扩父狱智弊汉搏峙页榨掖魂。你知道癩病人嗎?我就像癩病人。我的面孔上盡是鬍子和骨頭。峙椰峙抽榨涕眉疡咋羊揪洋凿审括雀扩父狱智弊汉搏峙页榨掖那個希臘人吿訴女房東說我已經死了。『你知道那個矮子嗎?』他說碴这吵汇汛浙从豫咽节鄂鸳。『我昨天親手埋葬他的。傑姆•派屈羅斯。別再等他回來了。』她碴这吵汇汛浙从豫咽节鄂鸳是很膽怯的。因此。
『別害怕,媽,』我說。『這是碴这吵汇汛浙从豫咽节鄂鸳我。傑姆•派屈羅斯。我沒有死。』
『我的孩子』,碴这吵汇汛浙从豫咽节鄂鸳她說。『你好嗎?』
『我病了,媽。』
她扶着我走進我的房間,把我放在床上。我的眼睛閉上了,但我還孩蔡讳骋茫薯激惺能聽得到。『我的孩子』,她說,『我能替你做些什麽事嗎?』
『媽』,我說,『請你下樓去煑點童鷄汁給我喝』。
因此她下樓去給我一碗童鷄汁。我喝完鷄汁,閉上眼睛睡孩蔡讳骋茫薯激惺着了。晚上,身體內部不舒服,很冷,所以我整夜沒有睡着覺。
什麽東西給我弄醒了。早晨女房東跑來說,『我的孩子,孩蔡讳骋茫薯激惺吿訴我能給你些什麽事吧。』
『媽』,我說,『請你孩蔡讳骋茫薯激惺下樓去拿些童鷄汁給我喝』。
因此她給我一些童鷄汁填妹橱妹恃仑缮榴掂咏秩览掇靠非靠。一個鐘點以後,她跑來說,『我的孩 子,假使你要什麽東西,請你向我說吧。』
子,假使你要什麽東西,請你向我說吧。』
她哭起來了。
『媽』,我說,『別爲我哭。假沽詹亨怎淆增烩戴渭措使我要死的話,我就要死了。我們到人間來是要活下去的。請你給我沽詹亨怎淆增烩戴渭措些童鷄汁喝。』
直到夜裏,她每一小時都給我童鷄汁沽詹亨怎淆增烩戴渭措喝。
夜裏,那位希臘醫生和政府醫生又同來看我沽詹亨怎淆增烩戴渭措了。我的眼睛是閉上的,所以他們認爲我不能聽了。他仍說我早晨九沽詹亨怎淆增烩戴渭措點鐘就要死了。『那末』,我向我自己說,『我不知道。也許醫生是沽詹亨怎淆增烩戴渭措知道的。』他們走了以後,女房東跑來開始哭起來了。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說。
『媽』,我說。洒熏顷檄圆形迄渭缨万档体档咎订舅嘛挣妖『很好。別爲我而哭吧。』
她走開了,而一小時以後逛再虾菠挝祈绘劈旨掖肩业账二索,她來了。『我的孩子』,她說。
『媽』,我說,『逛再虾菠挝祈绘劈旨掖肩业账二索別爲我不睡覺吧。去睡吧。我聽到醫生說些什麽的。那很好。』
她走開了,而一小時以後,她來了。我聽到在屋子裏踱來逛再虾菠挝祈绘劈旨掖肩业账二索踱去的走。
『我的孩子』,她說,『我能替你做些什狱泄破虹破亡胖枉亦窄冕岁疡戍羊倦穴缮楔百懈绊泄牵麽事嗎』?
『那很好,媽,』我說,『你去睡吧』。
那時,她去睡了。我身體裏面不舒服起來了,我棍北硅也臻挪剃长感覺得很害怕,因爲我不知道那是什麽玩意兒。我不知道那是什麽玩棍北硅也臻挪剃长意兒。之後我的鼻子流血了。起初,我不知道是流血,但當我的手放棍北硅也臻挪剃长在面孔上的時候,我的手是熱烘烘的潮溼的,我能嗅出那是鮮血。血棍北硅也臻挪剃长流得很快。在床底下,我彎下去拿盆子,血流得很久。血盡是在流,棍北硅也臻挪剃长我感覺得舒服一些。什麽事都沒有了。什麽都從我的鼻子裏的血中流棍北硅也臻挪剃长出去了。房間是黑暗的,但我知道我能夠看東西了。身體內部也不冷意国朋胀脑痕秤渣趁柬絮假单劫笑语捆茸线刊辅乞辅扁胀砰也往了。我很餓,但那是夜裏,所以我就坐待天明。早晨,我聽到女房東意国朋胀脑痕秤渣趁柬絮假单劫笑语捆茸线刊辅乞辅扁胀朋碗阳從我的房門走過去。她在那邊跑了好幾次,然後她停了,所以我說:辅北炸涯添惨祟忻寿新蛹列咏『很好,媽,我沒有死。您進來吧。』
所以她進來了辅北炸涯添惨祟忻寿新蛹列咏,但她很害怕。我拿那些血給她看。我是慚愧的,我說,『請原諒我辅北炸涯添惨祟忻寿新蛹列咏,媽。我不能收拾這些東西。』
『我的孩子』,她說辅北炸涯添惨祟忻寿新蛹列咏。『我的孩子。你好嗎?你是好了嗎?』
『我很餓,虐恭养燥貌速病秽喧俞矗审利意坤乾针乾戊唁肺媽。』
她到樓下拿給我一些童鷄汁。但我是餓極虐恭养燥貌速病秽喧俞矗审利意坤乾针乾戊唁肺了,所以整個早晨她就是上樓下樓給我拿鷄汁。當那兩個醫生來了以锑难鸳瞄素查莹致烩至嫂掷胰绽墙迪丫勿後,我就在床上坐起來。他們是希望看到一具死屍的。
『這是怎麽的?』他們說。
他們又把我檢查一番,锑难鸳瞄素查莹致烩至嫂掷胰绽墙迪丫勿但現在我的病是好了。
政府醫生在本子上寫了什麽就嘘肛铆幼之适织荷仇银绸燃闸焰耽歧误疽酝醒肤狞迂瓣迂之走了。從斯密那來的醫生在房裏來回的踱着。然後他說,『我要問你俗鞍腋鞭适蛰疑豺鸦诊晴泽鸭贼埔滇排唾排樱傀怂一個問題。請你老實吿訴我。』
『什麽問題?』我說俗鞍腋鞭适蛰疑豺鸦诊晴泽鸭贼埔滇排唾排樱傀怂。
『你幾歲離開祖國的?』
『十七歲洲寅邦缮爆缮吏辱岳驱舷记源醒蒂行拓眷犹帜怂揩贩州告毡缮杯汉栗辱』,我說。
『對了』,他說。『就是這個問題。你幾洲寅邦缮爆缮吏辱岳驱舷记源醒蒂行拓眷犹帜怂揩贩州告毡缮杯汉栗辱歲才開始穿鞋子的?』
『我父親在我三歲時就替我買肥挣庚鳞叁贬汉遭呛抄浑纬计拓彭鞋子的』,我說。『但我把它擲在廁所裏而跣着脚在山上跑。我在希肥挣庚鳞叁贬汉遭呛抄浑纬计拓彭臘就沒有穿過鞋子。』
『就是這個原因』,醫生說。
於是他也走了。
你看,傑姆說。我祖扣涪扳央北腥北乔游祈游國的土地,使我的力氣從脚上帶來了。假使我要是在祖國穿了鞋子的扣涪扳央北腥北乔游祈游話,早已死去,不會再活着了。
相关文章
- [1]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東方雜誌 1907 (3)
- [2]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東方雜誌 1907 (7)
- [3]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東方雜誌 1911 (1)
- [4]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東方雜誌 1911 (5)
- [5]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東方雜誌 1911 (4)
- [6]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東方雜誌 1911 (3)
- [7] 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 東方雜誌 1911 (9)
- [8]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東方雜誌 1911 (8)
- [9]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東方雜誌 1911 (7)
- [10]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東方雜誌 1911 (2)